性、蟲與過癩--明清中國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
性、蟲與過癩──
明清中國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
蔣竹山
我所要描述的不是移居到疾病王國、住在那的真正情
狀,而是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
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Susan Sontag, 1978)
明清中國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
蔣竹山
我所要描述的不是移居到疾病王國、住在那的真正情
狀,而是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
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Susan Sontag, 1978)
中文摘要
以往史學界的痲瘋病研究大多集中在以醫學史或社會史的角度探討痲瘋病的疾病概念、病徵特色與醫家看法等,例如梁其姿的〈中國痲瘋病概念演變的歷史〉與李尚仁的〈種族、性別與疾病──十九世紀英國醫學論痲瘋病與中國〉。少有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疾病與社會的關係。本文主旨不在探討明清痲瘋病的疾病本身及真實面貌,而是著重分析疾病的再現與隱喻,主要透過明清時期的一些小說與筆記等文本,探討明清有哪些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這些社會想像是如何建構出來的?如何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實際操作與處置措施?與痲瘋病患者的社會處境有何關聯?
性、傳染、蟲、蛇、毒、痲瘋女與過癩似乎是明清社會對麻瘋病的共同的社會想像。據梁其姿的推測,這可能與受了楊梅瘡(梅毒)傳入中國兩廣一帶的影響有關。這從《解圍元藪》可看出端倪,沈之問將癩病與楊梅瘡混為一談,並且舉出閩粵地區的過癩習俗,可能加重了當時醫界與社會對麻瘋病的誤解。此外為何明清時期的嶺南地區會被認為因特殊的地理環境與體質而特別容易感染到痲瘋病?事實上,明清之前不乏北方的大風/癘/癩病患者,但由於主流的南方醫者的社會想像與觀察偏差,使得楊梅瘡在閩粵一帶的肆虐影響了這種地理差異的想像。另一個可能是當時醫家大多南方人,所以目光大多集中在南方的風土病,而無視北方的情況。
明清時期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中,無疑地,過癩是小說作者目光聚集的焦點。痲瘋病在明清時期與性、蟲、毒與過癩等形象相結合,一改中古時期痲瘋病給人不道德的宗教意象。明清的醫者或社會大眾似乎相信痲瘋病的性格類型的存在――得痲瘋病與淫蕩的性有關。儘管痲瘋病被認為不只是可怕的病也是醜陋的病,但與痲瘋病相關的過癩文本卻美化了痲瘋女的形像;相對而言,登徒子或尋芳客的形像被描述為逞一時之樂的好色之徒,在這些文本中痲瘋病如同十九世紀西方的梅毒一樣――似乎訴說著痲瘋病是對不正常的性的逞罰。如同當代許多人相信癌症性格類型的存在一樣,現代癌症神話易將癌症患者想像成無感情、抑制與壓抑的人。如果我們難以想像痲瘋病的真實面貌為何能夠如此荒謬地被轉化,我們不妨考慮二十世紀另一惡名昭彰的病――AIDS。透過小說的訊息傳播,嶺南地區的過癩想像成了全國皆知的痲瘋病形象,這種熟知,不只是觀念上,而且反映在實際慣習上。換言之,小說在過癩習俗的傳播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關於這點,我們若從不同時期的賣瘋女的版本作一詳細的比對,似乎可以發現彼此之間無論在結構、內容或痲瘋想像上都相當類似,並且前後有相互參照與影響。
本文經東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蔣竹山老師同意,全文轉載
性、蟲與過癩──
明清中國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
蔣竹山
前言
一、性、在室女與過癩
二、蛇、蟲與毒的想像
三、想像與隔離
結語
我所要描述的不是移居到疾病王國、住在那的真正情
狀,而是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
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Susan Sontag, 1978)
前言
Susan Sontag曾在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中提到,痲瘋病在全盛期曾引起西方社會極大的恐懼,在中世紀時,痲瘋病患者是腐敗社會的象徵與教誨的啟示,沒有比賦予該病道德意義更具有懲罰性的事了,任何病只要起因不明、治療無效,就容易為某種隱喻所覆蓋。例如一些腐敗、墮落、污染、社會的反常狀態常會與痲瘋病一詞相連結,有時痲瘋病會成為形容詞,例如在法文裡,一座模製的石頭立面被稱為 “lépreuse”,意指「患痲瘋的、痲瘋患者」。 相較於西方將痲瘋病污名化的態度,中國也有類似看法,比較特別是華南地區的「過癩」慣習。1937年5月16日作家周作人在《晨報副鐫》寫了一篇雜文〈談過癩〉,文中轉引《實報》「美的新聞」中的一篇新聞〈痲瘋傳逼粵中〉,該則新聞提到,廣東省當時正流行痲瘋病,有人主張仿效西方取締劣等民族的辦法,一律處以槍決,律師葉夏聲上電反對,最後廣東省省主席吳鐵城則採取人道立場、科學精神來面對此事,結束了鬧的滿城風雨的紛爭。此外該文說廣東地區之所以會盛行痲瘋,是因為該地氣候溼熱,嵐瘴蒸鬱所致,福建有也這種病,但不及廣東之多。這種病症男女都有,患者會全身擁腫,奇癢無比。該病會傳染,但與飲食無關,但男不傳男,女不傳女,必定是異性相傳,並且只透過性交才能傳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現象有個專門的術語叫「過癩」。事實上,周作人並非第一位報導廣東地區有「過癩」現象的作家,相關的生活慣習早在宋代就已有類似記載,甚至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中葉。六O年代時美國痲瘋病專家O. K. Skiness曾在香港進行麻瘋病的田野調查,他發現中國人對麻瘋病的幾點共同看法:(1)麻瘋病被認為是因為道德上的罪行所引起。(2)麻瘋病被等同於性病同樣的病。(3)患者身上的分泌物、體熱、皮膚碎片是有毒性物質。(4)麻瘋病會遺傳三代。(5)麻瘋病可經由性行為而感染。Skiness的研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何六O的香港居民會有痲瘋是種與性有關的疾病?這樣的觀念從何而來呢?
上述Sontag 這種探討文學中的疾病隱喻或社會想像的取向對後來西方醫學史界的社會史走向有重要啟發,像Roy Porter 與Sander L. Gilman 的部分著作多少受到影響。 這樣的研究取向在台灣並不多見,以往史學界的痲瘋病研究大多集中在以醫學史或社會史的角度探討痲瘋病的疾病概念、病徵特色與醫家看法等, 例如梁其姿的〈中國痲瘋病概念演變的歷史〉與李尚仁的〈種族、性別與疾病──十九世紀英國醫學論痲瘋病與中國〉。 少有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疾病與社會的關係。本文主旨不在探討明清痲瘋病的疾病本身及真實面貌,而是著重分析疾病的再現與隱喻,主要透過明清時期的一些小說與筆記等文本,探討明清有哪些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這些社會想像是如何建構出來的?如何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實際操作與處置措施?與痲瘋病患者的社會處境有何關聯?
一、性、在室女與過癩
明清之前,有關痲瘋病的論述大多集中在痲瘋病是一種天刑病。先秦時就已出現這種觀念, 但明確指出因觸犯宗教禁忌而患「白癩」的看法,要等到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帶來業罰及天刑病的思想後才較為普遍 。在佛教的觀念裡,痲瘋病之所以是所有疾病中最難治的病,是因為患者犯了宿命罪的緣故。此外,我們在宋代《太平廣記》中,亦可發現不少類似的資料,其內容不外乎侮篾或毀壞佛像後會得癩病。 但到了明清,天刑病的說法不是沒有,卻觀念已經漸變薄弱,像清閔鈦的《蕉窗十則註解》所指:「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置身通顯;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的例子已不多見, 取而代之的是有關痲瘋女過癩的文類。
明清社會有關痲瘋病的故事最具特色的就是痲瘋女──而且是在室女的「過癩」風俗。當時在兩廣一帶盛行一種名叫「過癩」的傳說,這些傳說得以廣為流傳的原因與通俗小說的創作與流通有著密切關係。過癩的故事結構大多是,當地女子在發現有面如桃花狀的痲瘋病初期病徵時,即表示已受到感染,其治療方式是,痲瘋女聯合家人,共同設下圈套,色誘外來不知當地過癩習俗的男子與其發生性關係,事後不久,該男子就會因此染上麻瘋而死,而原痲瘋女則痊癒,這就是當地人所謂的「過癩」。
目前所見最早記載「過癩」傳說的是十三世紀末,宋代周密(1232-1298)《癸辛雜識》〈過癩〉可能是日後所有痲瘋女故事的源頭。 該則故事記有,福建地區所謂過癩者。大多是女子感染,凡感覺面如桃花,就表示已經受感染。有些外來男子不知實情,常會與過癩女子發生關係,如此癩病就可轉給男子。當地人都熟知這個習俗,並常用此方法誘騙外來者。 遍查唐代有關痲瘋病的記載中,未曾發現有任何「過癩」的說法,我們推測過癩的故事原型可能在宋代才出現。
「過癩」又稱「賣瘋」或「過瘋」,到了明清,有關過癩習俗的文類大量出現,舉凡詩、筆記和小說中都可見到痲瘋女的蹤影,這些文本的結構與故事情節大多類似,並有前後文本相互影響的現象。明人王臨亨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奉命到廣東審案時,記錄了途中的見聞,寫下了《粵劍編》一書,書中記有當時廣東人多患有痲瘋病,其中男性佔了約十分之八、女性約佔十分之三左右,他的估計與明正德年間薛己《粵劍編》所收痲瘋病醫案的男女比例大致吻合;地區則以雷陽一帶最盛。其病徵剛開始時,是出現於指爪間,但不會感覺痛癢。女子一旦患有此病,即假裝私奔,用以引誘男子與之發生性關係,事後,痲瘋女的病就可完全轉移至男子身上。
清代之後,痲瘋病的故事幾乎多以描述痲瘋女過癩的故事為主。例如:《咫聞錄》〈痲瘋〉記有:「為女瘋可賣,而男瘋不能。嘗聞有絕色女子,鉤引少年子弟,一宿之下,其瘋即過,是女之瘋即脫,少年再覓,不再見是女矣。男即眉落,醫之無益,此只可賣與外江之客,不能種於土人也。故諺有少不入廣之語。」 這則例子和明代和明代王臨亨所說的類似,不過有一點很重要,作者點出了該風俗的特性是女瘋可透過性交轉過給男性,男瘋則不可。《續客窗閒話》〈烏蛇已癩〉更描述了廣東潮州府一帶,當地幼女皆染有癩毒,所以年屆十五,就必須靠有人過癩才可配婚。因此該地痲瘋女在十五、六歲時,不論貧富,皆會在大門外工作,藉機引誘外來的浪子,一旦雙方交往彌月之後,女方父母就會張燈結彩,設筵款待親友,表明女癩已去,可結親矣。該浪子也會參與宴會,事畢,富者就會贈一筆醫金打發浪子離去,但通常不到一年浪子就會發病而死。
廣東痲瘋女引誘男子過癩的方式可謂是五花八門,除了上述例子外,尚有假集體賣酒之名,行賣瘋之實。清.屈大均(1630-1696)《廣東新語》〈瘋人〉這則短文中記有:廣東仙城地區有許多麻瘋病的男女患者行乞道旁,所遺留的穢氣最容易使人感染痲瘋。其中又以廣東西部的高州府及雷州府因盛行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居民生瘋的相當多,由於情況相當普遍,當地居民都視之為是「祖瘡」而不覺奇怪。除了此地的痲瘋病患者特多之外,屈大均還發現當地盛行「過癩習俗」,其地域分布遍於從陽春到海康一路六、七百里的板橋與茅店之間。當地有些賣酒婦女,腰間會繫著盛滿水果的花繡囊,等有客商經過時,就牽人下馬獻之。這些賣酒婦之中,十之五六是痲瘋病者,他們如此慇勤地招攬客商,目的不外是欲藉機找「過癩」的對象而已。
此外,清.宣鼎的《夜雨秋燈錄》〈痲瘋女邱麗玉〉這則故事中,提到廣西邊境代產美人,但都遺傳有痲瘋病,女子十五歲一到,富家常以千金誘遠方人來過毒,毒盡才與人論婚嫁;若期到不過毒,則會疾根頹發與膚燥髮拳。 宣鼎這則事例很清楚的點出女子過癩的年齡下限是十五歲,過此年限,可能就會失效。至於過癩者的下場如何,宣鼎描述的較前面幾則要詳細:若外地人不慎與痲瘋女交媾的話,三四日即項有紅斑,七八日即遍體騷癢,一年多後身體就會拘攣拳曲,其發病過程雖和緩,但最終仍難逃病死。
明清過癩的習俗不僅被用來治療痲瘋病,有時鄉民會借用此習俗對付外來的駐軍。《南越遊記》記有道光年間中英鴉片戰爭時,英軍攻粵,清政府調動各省軍隊協防,其中湘軍凶悍不法,廣東居民敢怒不敢言,因此暗遣痲瘋女誘惑湘軍,湘軍因感染痲瘋病而死傷者過半,最後返回湖南者只剩不到數十人。 對於過癩所引發的傳染問題,當時一些詩人常感慨萬千,光緒年間的《嶺南雜事詩鈔》〈賣瘋〉就記有:「桃花莫誤武陵源,賣卻瘋時了夙冤,也是貪歡留果報,待回頭已累兒孫」。
兩廣地區的過癩傳說所以能夠廣為流傳的原因之一,我們認為與晚清通俗小說的普遍刊行有關。許多晚清小說都會將過癩故事──尤其是《續客窗閒話》的〈烏蛇已癩〉加入小說劇情中,例如吳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與坐花散人編的《風流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述一位上海人到廣東遊歷,碰到一位潮州人向他抗議《續客窗閒話》中的過癩傳說污衊潮州婦女形象的故事:
述農一面看日記,末後指著一句道:「這《續客窗閑話》毀於潮人是甚麽道理?」我道:「不錯。這件事本來我要記個詳細,還要發幾句議論的,因為這天恰好有事,來不及,我便只記了這一句,以後便忘了。」我在上海動身的時候,恐怕船上寂寞,沒有人談天,便買了幾部小說,預備破悶的。到了廣東,住在名利棧裏,隔壁房裏住了一個潮州人,他也悶得慌,看見我桌子上堆了些書,便和我借來看。我順手拿了部《續客窗閑話》給他。誰知倒看出他的氣來了。我在房裏,忽聽見他拍桌子跺腳的一頓大罵。他說的潮州話,我不甚懂,還以為他罵茶房;後來聽來聽去,只有他一個人的聲音,不像罵人。便到他門口望望。他一見了我,便指手畫腳的剖說起來。我見他手裏拿著一本撕破的書,正是我借給他的。他先打了廣州話對我說道:「你的書,被我毀了。買了多少錢,我照價賠還就是。」我說:「賠倒不必。只是你看了這書為何動怒,倒要請教。」他找出一張撕破的,重新拼湊起來給我看。我看時,是一段《烏蛇已癩》的題目。起首兩行泛敘的是:「潮州凡幼女皆蘊癩毒,故及笄須有人過癩去,方可婚配。女子年十五六,無論貧富,皆在大門外工作,誘外來浮浪子弟,交住彌月。女之父母,張燈彩,設筵席,會親友,以明女癩去,可結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道:「這麻瘋是我們廣東人有的,我何必諱他。但是他何以誣蔑起我合府人來?不知我們潮州人殺了他合族,還是我們潮州人辱了他的祖宗,他造了這個謠言,還要刻起書來,這不要氣死人麽!說著,還拿紙筆抄了著書人的名字──「海鹽吳熾昌號薌斥」,夾在護書裏,說要打聽這個人,如果還在世,要約了潮州合府的人,去同他評理呢。」述農道:「本來著書立說,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麽好胡說,何況這個關乎閨女名節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
我道:「因為他這一怒,我倒把那廣東麻瘋的事情,打聽明白了。」述農道:「是啊。他那條筆記說的是癩,怎麽拉到麻瘋上來?」我道:「這個是朱子的典故。」他注‘伯牛有疾’章說:「先儒以為癩也。據《說文》:‘癩,惡疾也’。廣東人便引了他做一個麻瘋的雅名。」繼之撲嗤一聲,回過臉來,噴了一地的酒道:「麻瘋還有雅名呢。」我道:「這個不可笑,還有可笑的呢。其實麻瘋這個病,外省也未嘗沒有,我在上海便見過一個;不過外省人不忌,廣東人極忌罷了。那忌不忌的緣故,也不可解。大約廣東地土熱,犯了這個病要潰爛的,外省不至於潰爛,所以有忌有不忌罷了。廣東地方,有犯了這個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認的了,另外造了一個麻瘋院,專收養這一班人,防他傳染。這個病非但傳並且傳種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來,然而骨子裏還是存著病根。這一種人,便要設法過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設法。那女子卻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過一兩回就過完了。那上當的男子,可是從此要到麻瘋院去的了。這個名目,叫做「賣瘋」,卻是背著人在外面暗做的,沒有彰明昭著在自己家裏做的,也不是要經月之久才能過盡,更沒有張燈宴客的事,更何至於闔府都如此呢。」繼之愣愣的道:「你說還有可笑的,卻說了半天麻瘋的掌故,沒有可笑的啊。」我道:「可笑的也是麻瘋掌故,廣東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如靴業祀孫臏,木匠祀魯班,裁縫祀軒轅之類,各處差不多相同的。惟有廣東人,那怕沒得可祀的,他也要硬找出一個來,這麻瘋院當中供奉的卻是冉伯牛。」
上述對話中提到痲瘋病會傳三代的觀念在許多筆記中都有類似說法,例如《兩般秋雨盦隨筆》的〈痲瘋女〉也說廣東有所謂痲瘋者,沾染後無藥可救,所以到處皆有設痲瘋院,患者在院裡相互通婚,通常有無傳染要三代才看的出來,因此三代後才可以出院。 另外一部小說《風流悟》則是提到廣西潯州府地區盛行十四、五歲的女子主動找男子過癩的風俗:
畹香道:「兩位老弟,我們這樣人才,自然為天下美女所愛的,但不可輕瀆了。後日娶妻房,同要揀個極美的,倘本地沒有,不妨在他州外府去。」連城道:「有理。我正有個願心,意欲要去完一完。」澹仙道:「二哥有什麽願心,我與你完成。」連城道:「有一個母舅,住在廣西潯州府,那潯州府風俗,與另處不同。別處男子尋女人,潯州府是女人尋男子的。他們更有個尋法,有趣得緊。」畹香道:「怎麽有趣?」連城道:「他們閨女到十四五歲,要先尋個男子過癩。過癩了,然後每年春間打扮了,到名山勝行遊玩,到尼姑庵裏燒香,廣采輿論,定個高下。」
明清筆記與小說對痲瘋病人的心理、社會處境、家人反應、以及所引發社會問題的敘述篇幅的明顯增加,似乎反映了痲瘋病已成為當時的社會問題。明清時期有關痲瘋病的論述較特別的看法有二,一是痲瘋是種地方病,而且大多在南方,另一個是中古以來痲瘋病是天刑病的論述漸漸薄弱,而被痲瘋女的「過癩」故事所取代,特別是強調「性」的部分。性、婦女與痲瘋病的結合成了清代通俗小說中痲瘋病故事的主要類型。癩病為何跟性牽連在一起,為何女瘋可過,而男瘋不行?這似乎與明清對痲瘋病的社會想像有關。基本上,明清社會把痲瘋病視為一種兩廣地區特有的地方病,並把這這種病想像成是種會經由性行為感染的傳染病。民間醫者對過癩現樣的解釋也加深了民眾的觀感。對此《瘋門全書》有詳盡的解釋,蕭曉亭認為男痲瘋傳給女的極少,大多是女痲瘋傳給男的。女痲瘋病者較少的緣故,主要是女性可經「過癩」傳給男性。患麻瘋的處女之所以能將痲瘋移轉給男子的原因之一,又與女子透過初經來時將瘋毒排出有關,因此蕭氏從民間的過癩習俗得一些較為和緩的治癩靈感,醫者可在處女初經來時,配合藥物治療,去除體內血熱,如此毒素才會完全排出。蕭氏並認為蕭曉亭以醫者身份,首次將盛行民間數百年之久的過癩習俗做醫理上的解釋,並進一步其原理應用到以藥物配合女性生理週期來治療癩病。 這不僅代表民眾的日常慣習與社會想像對民間醫者的醫療行為頗有影響,亦反映了過癩的觀念及習俗在當時廣東確實盛行,才會引起醫者的注意。
痲瘋病在明清的醫書或士人筆記中是如何呈現的呢?清代醫者蕭曉亭是位地區型的醫者,名雖不見清代各大醫書,但所著《瘋門全書》卻是相當詳盡的分析了此病的地方特殊性。當時中國東南沿海所盛行的「痲瘋病」,在廣東被稱為大痲瘋,俗名「疙瘩」,廣東以外地區則稱做為大皮瘋,又名癩皮瘋。 痲瘋病被稱做「痲瘋」的說法是在明清之後才較為普遍,在此之前,多稱為癘、惡、癩、癩風與大風等等。 當時人認為痲瘋病的地域分布大都位於長江流域以南;其中,又以廣東的例子最多,其次是廣西、福建。例如,明薛己的《癘瘍機要》中就載有痲瘋病多發生於「淮揚嶺南閩」地區的說法。 梁紹任的《兩般秋雨盦隨筆》則記有粵東有所謂痲瘋者,沾染以後,不可求藥。 清代吳震方的《嶺南雜記》說潮州大痲瘋極多。 庸訥居士《咫聞錄》則記兩廣多痲瘋。 清人宋翔鳳(1776-1860)的詩更直指廣東嶺南一帶多痲瘋。 道光二十五年(1899)廣東敬業堂重刻的《瘋門全書》序中亦寫道:廣東多痲瘋; 另同書序三中亦說:「痲瘋是因為地氣所造成,東南地區最為嚴重,長江以北沒有這樣的例子。」 華南地區的痲瘋病病例真的比較高嗎?醫者何如解釋此現象呢?《咫聞錄》的看法是該地區地勢低窪潮濕、天氣過暖的緣故。清代青城子《志異續編》則認為各省因地氣不同,所以病況會不同,例如廣東多痲瘋,是因為地氣炎熱,潮濕往來,蘊結蒸鬱,上煙瘴不正之氣,因此此地居民較易染病。」 醫家蕭曉亭對此則有較深入的看法,他認為傳統醫者不知痲瘋病的病源,有人說是傳染,有人說風水,其實這些原因都有可能 ,因此特別強調地域環境特性與疾病產生的關連。他認為,東南地區地劫低窪近水的地方,痲瘋病的例子較為普遍,這是因為在熱氣與溼氣的交互作用下,易生穢氣,在人身體較虛弱時,才會影響到人體的衛氣與營血,進而凝結於筋絡,沈積於肌膚之間。 又在何種情況下,人體氣血較虛呢?《瘋門全書》舉了一些實例,凡是睡在溼地上受到薰蒸﹔或是吃汗後洗冷水澡﹔或穿濕衣服﹔或房事後洗冷水,皆有可能得病。 這幾種易接觸濕氣的生活習慣,配合東南地區的特殊地理氣候環境,增加了當地人感染痲瘋病的機率。
二、蛇、毒與蟲的想像
明清過癩的傳說似乎一直流傳到現在,現今大陸大連外海有個蛇島,至今還流傳著蛇酒能治痲瘋病的傳說。當地的說法是這樣的:傳說蟒山蛇酒能治麻瘋病。那時得了麻瘋病,用什麽藥也治不好。有位姑娘找婆家,因得了痲瘋病,按常例她必須和別的男人住上幾天,把麻瘋病傳給他,再和自己的丈夫結婚。 這叫「放風」。這位姑娘說什麽也不肯,病情逐漸加重,臥床不起,無奈拿起酒罎子,以酒當水喝了好幾大口,借酒肖愁,麻醉自身,以求速死。誰知酒下肚,頓生奇效,自覺身體輕鬆,象沒得病似的。未過幾日,病癒體安,端來鏡子一照,自己大吃一驚,依舊是花容月貌,不減當年美。親人們問她病是怎麽好的,她也說不清,只說口渴喝了幾口酒,衆人看酒壇,只見壇裏有條大白蛇。原來是大白蛇從房柁爬到酒壇偷酒喝,淹死在酒壇裏,消息傳開,人們醒悟道:麻瘋病遇蛇毒,以毒攻毒,蛇酒能治麻瘋病。從此,蛇酒能治麻瘋病的妙方流傳至今。這樣的傳說在中國北方的大連出現,一來似乎說明了過癩傳說已不限於南方地區,二來凸顯了通俗小說對明清社會訊息的流通的影響力頗大。事實上,大連蛇島的故事綜合了幾篇明清小說的內容。明清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除了與「性」有關外,尚與「毒」有關。而有關毒的想像又可細分為是體內穢氣引起的毒與「癩蟲」引起的毒。
痲瘋病的症狀由於很像是體內毒素引起的皮膚病,所以通常民間的做法是採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排毒,例如唐以來就常見吃烏蛇、長松、砒霜及松脂等, 到了明清則以誤食烏蛇酒而治癒癩病的故事最多。這種療法似乎是建立在中古以來民間社會對蛇與蟲的想像基礎上。清人吳熾昌於光緒元年(1875)刊刻的《續客窗閒話》〈烏蛇已癩〉即是此類故事的代表,這篇記載提到潮州知府曹太守的弟弟,不聽告誡,貪圖美色,與患痲瘋病的富家女子發生關係,二人相處彌月之後,曹弟因染上痲瘋病,而被送回原籍等死,一路上毛髮脫落,日漸全身發癢,返家後病發奄奄一息,由其二哥收容,因死其病情蔓延,遂將他關於酒房中,後因口渴誤喝有烏稍蛇掉入缸中的酒而「癩皆結痂,人亦清爽。」 ,當曹弟發現烏稍蛇酒對治療痲瘋有效後,就在每餐飯前連續喝了半個月,果然就癩痂脫落,長出一身新肉,不但皮膚滑膩,而且眉髮復生,面貌宛如風流少年 。
有關民間以烏蛇酒治痲瘋的觀念可上溯至唐代,當時民間相當流行以烏蛇當作治療痲瘋的藥方。其中,大多是以烏稍蛇泡酒飲用,例如,唐代張鷟《朝野僉載》記有:陜西商州地區有人患了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酒器中,病人不知,飲酒後漸漸痊癒,最後才發現是罐底有蛇骨的緣故。 此外有單食蛇肉去瘋的例子,泉州有位叫盧元欽曾感染大風,在旁人推薦下,遂取一截蚺蛇肉來吃。不到五日就漸感病況轉好,百日後就痊癒了。 有時蛇酒亦非萬靈丹,若使用不當,很容易喪命,明代葉權(1522-1578)所撰《賢博編》即載有蘄蛇酒可治瘋癩病,但不可濫用。曾有少年無故喝了數杯即死去。又有陳姓老婦誤以為喝的是烏稍蛇酒,最終遍體撞裂流黃水。 蘄蛇就是白花蛇,和烏稍蛇齊名,同是治療痲瘋病的藥方,《瘋門全書》九十五種配方中,以白花蛇為藥方的有十五種,烏稍蛇只有三種,有趣的是,目前文獻所見,民間大多用烏稍蛇酒治痲瘋,像葉權舉的非痲瘋病患者而飲蘄蛇酒的例子,倒是少見,第一條資料反映了烏稍蛇和白花蛇在民間都有互用的可能性。第二條則透露,在烏稍蛇酒可治痲瘋病的說法流傳後,當時可能有些民眾如同陳婦一樣,誤將其它蛇當作烏稍蛇配酒飲用,結果發生中毒的現象。除了蛇酒外,清代采蘅子《蟲鳴漫錄》中記有一則民眾因誤食參有蛇涎的食物,而治愈痲瘋病的例子。
其實以帶有毒性的蛇酒做藥方,本身就帶有危險性,再加上處置失當,常會害人喪命,唐代李肇《國史補》〈療風醞蛇酒〉即記有:「李舟之弟患瘋疾,或說烏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嘎嘎蛇聲.數日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之,斯須悉化為水,唯毛髮存焉。」 李舟之弟化為一攤水的死狀,的確駭人聽聞,這則故事多少反映了飲烏稍蛇酒的危險性。明清民間這種擅自用以毒攻毒手法治痲瘋的例子,除了烏稍蛇酒外,還有服砒霜的,可見當時此種劇毒偏方種類之多。對於民間的這些作法,醫者蕭曉亭認為痲瘋雖是惡疾,但治之得法的話,即使常用溫和的藥,也應有效,至於蛇蠍都還算是安全的藥方,唯有到了病重時才可用用到砒霜、蜈蚣、斑螫、輕粉等劇毒之物,但不可過份依賴 ,蕭氏的看法多少反映了以毒攻毒的治癩觀念在當時民間應相當普遍。
明代許浩《復齊日記》記有一則江西人陳壽服砒霜治例癩疾的例子:有位名叫陳壽的分宜人,因患了癩疾,未婚妻的父親令她辭退婚事,但該女堅決完婚,最後兩人終於成婚。婚後陳壽病況加劇,不願陳妻靠近,但陳妻依然服侍他三年。陳壽感念惡疾無法痊癒會拖累陳妻,因此暗地裡買了砒霜欲自盡,後被陳妻知道偷喝了一半,希望兩人同歸於盡,不料陳壽卻因此因禍得福,得以痊癒。故事最後以喜劇收場,兩人最後白頭偕老,生下三子且家道日隆。
這則事跡是明正德年間任南京戶部尚書的李瀚(1453-1533)告知許浩的,而出被於一六二七年的馮夢龍小說《醒世恆言》收入一篇情節類似的作品〈陳多壽生死妻〉,據推測可能是馮夢龍根據許浩一文改編。馮氏一文中對痲瘋病患的病徵、家庭反應、延醫成效、服砒霜自殺及事後痊癒等情節有非常詳盡的描寫,多少亦反映作者對當時痲瘋病的社會想像。文中陳多壽初得痲瘋病時,只以一般的皮膚病──疥癬看待,不料一年後,形體容貌竟變的不成模樣,對此病徵,作者有非常生動又寫實的描述:「肉色焦枯,皮毛皴皺。渾身毒氣,發成斑駁奇瘡,遍體蟲鑽若殺,晨昏作癢。任他凶疥癬,只比三分,不是大痲瘋,居然一樣。粉孩兒作蛤蟆相,少年郎活像老龜頭,搔爬十指帶濃腥,齷齪一身皆惡臭。」 。痲瘋病患服用砒霜後的反應,我們透過〈陳多壽生死夫妻〉一文,有了初步的了解,當陳多壽夫婦同喝砒霜酒昏倒後,碰巧被陳母見到,陳父趕到後見酒壼中尚有砒霜殘餘,因為知道一種取生羊血餵食就可活命的單方,兩人就在灌下羊血,登時嘔吐的情況下才甦醒,之後餘毒留在腹中,不久皮膚迸裂,流血不己,調養了一個多月,才飲食如故,最後毒氣氛洩盡,瘡痂脫盡,依舊頭光面滑,肌細膚榮。陳多壽患了十年的癩症,請了若千名醫部無效,最後卻服了毒酒才好,在作者看來正印證了醫書中「以毒攻毒」這包話。
最後一則驅蟲法的例子,則是清.庸訥居士在廣西所聽說的,當時伊藤縣有富翁忽患麻瘋病,後惟恐傳給子女,就另外築屋獨居,靠妻子早晚送食,某日僕人將一碗雞肉置於熟睡的富翁旁,後妻子進入探視時,竟發現椅上有許多狀似白糠、堆積如毬的蟲正在食雞肉,遂迅速取布裏至院裡,用火燒之;此後,不到一個月,富翁的病就痊癒。庸訥居士對這則故事的解釋是:「夫濕熱生風、風生火、風火生蟲、,理固然也。今以雞而引蟲具出,亦一善醫之法也。」 康訥居士認為,傳統醫者只知以去風、收濕的方式來治痲瘋病,但效果有限,卻不知患者體內的蟲亦是是引起麻瘋病的病源之一,因此只要把蟲引出消毀,不治之症自然就會好。 有關疾病與蟲的意象與關聯,除了痲瘋病的例子外,肺癆亦曾被視為是人體內有蟲在作怪。
除了靠外物將蟲逼出或引出外,另外有些是藉由過癩方式將體內的蟲排出的例子。像《珊瑚舌雕談初筆》〈過癩〉就說到:癩蟲自男女經液中排出,才容易痊癒。該書還提到該如何除蟲,例如男性欲除癩蟲,可用荷葉將陰莖包覆,置入女體內,待性交射精後抽出荷葉,如此精液與蟲都會包裹在內,然後丟棄,這有兩個好處,一是不會射精至女體內,二是對女子無害。或許癩蟲的社會想像可以解釋為何明清兩廣一帶居民相信過癩得以治癒痲瘋病,但仍有部分地方與上一節所說的過癩不同,此例反映了男性也可以透過性交將癩蟲排出的社會想像。
此外我還可以在明清社會發現透過玉辟邪氣、飲用神仙酒與驅蟲法的治療法。清代青城子《志異續編》記有,廣東香山縣有個蜑戶捕魚時撈到一六、七寸色黑的光滑石頭,後被一織匠買去磨布,日久黑色漸退,才發現內臟一塊圭玉;此後,織匠日夜掛於身上。原本此人既患有痲瘋病,自從佩帶此圭璧,舊疾就不再復發,而且自然痊癒。清城子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玉原本就可以潤心肺、滋毛髮,又經鹹水浸沃已久,其效果自然較玉強數倍,而痲瘋原本是不正之氣所成,血熱皮燥,經過玉氣的滋潤,因此才沒復發 。清代梁章鉅(1775-1849)《浪跡叢談》記有:神仙酒乃國初江南趙尚書傳自康親王,趙素患風疾,後得此方飲之,宿疾頓除,夫婦俱活到九十餘歲,這貼藥方才遍傳於人 。
三、想像與隔離
明清社會對痲瘋病的想像不僅左右了民眾日常生活的慣習,亦影響到官員或士紳的處置態度與措施。一般來說,感染痲瘋病的患者外型會有顯著的變化,宋翔鳳在一首〈痲瘋院〉詩的前半段,對痲瘋病患的病徵有詳盡的描述:「嶺表有異疾,卑溼感毒淫,始發桃李紅,紅暈頰輔深,徐散成斑連,周身靡不侵,面目久模糊,語莫辨其音,蘊熱吐臟腑,出氣難自禁。 」醫者蕭曉亭的形容更為逼真。病況輕微者剛開始由於皮膚血滯不行,漸生痲痺,背腰手足之間,形如疥癬,患者不知痛癢,即使用針扎亦無感覺,有時頭面或似蟲行,或手足骨節間,撞之如刺痛。到了病重時,手足生瘡,肉中結核,臉紅耳腫,口堝眼斜;年久即壞形變貌,鼻塌肉崩,手指脫,落足底爛穿。到了這些面目猙獰的病徵出現時,就相當難治了。 明清時期的痲瘋病患者常成為社會的邊緣人,這種遭遇與麻瘋病患的上述病徵有密切的關係。當時痲瘋病患的悲慘命運,蕭曉亭清楚地描述如下:「夫癘疾也,得之者,父子離散,夫妻睽違,戚友避之,行道叱之。非若他疾只傷一人,癘實傳染常多,或傷鄰友,或傷一家,至於無與為婚而絕嗣者不少。」 由於當時普遍認為痲瘋病有傳染性,再加上患者本身病徵的恐怖模樣所帶給人的畏懼感,因此痲瘋病患與其它疾病患者相較,較不易使人接受。所以有些患者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情況下,不乏投水懸梁,自戕其命的例子。痲瘋病的殘酷在當時人看來,實在瘟疫還要嚴重。
一旦痲瘋病成為一種醫學論述下的特殊疾病──特別是與華南地區有關的「地方病」的時候,尤其在「過癩」習俗的社會想像的推波助攔下,痲瘋病患者生存問題就成為公眾問題,此時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就明顯地劃分開來,本地與外地的觀念也越加強化,「隔離」成了社會解決此一問題的唯一管道。
近代中國對痲瘋病的看法一直要到西方醫學傳入後,部分地區才陸續有較科學的醫療措施。 一九二六年中華痲瘋救濟會在上海成立,並於一九二七年發行了機關刊物《痲瘋季刊》,為我國最早研究痲瘋病的刊物,其宗旨在介紹最新痲瘋學理和藥物、灌輸痲瘋教育、提倡科學治療、鼓勵鏟風運動、討論推動痲瘋救濟運動、及報告國外痲瘋消息。 直到一九三0年代,醫界才能較有效地控制痲瘋病的病情,此外在知識分子的大力推動改革與設立新式的痲瘋院後,對於痲瘋病的隔離治療才較有成效。儘管有這些醫學措施,但民間普遍對痲瘋病還是心存疑慮,這從晚近中國大陸仍存有許多「痲瘋村」可以看出端倪。為何民間的反應會如此激烈?這與自明清以來,民眾對痲瘋病的社會想像有著密切關係。明清社會將痲瘋患者與世隔離的做法,其實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痲瘋病的社會想與集體恐懼心態。
事實上,據現代醫學觀點來看,痲瘋病並不如過去人們所認為的那麼容易傳染。明清時人大多認為痲瘋病很容易傳染,例如《清稗類鈔》記有,清代後期湘軍中有許多人在廣東地區駐紮時染上痲瘋病,由於擔心死後運回家鄉會傳染,乃採取火葬做法處理屍體,或許是死亡數量太多的緣故,常造成木柴需求量增加,致使木柴漲價,廣州因而出現「燒貴柴」一詞,用來譴責外地人破壞當地的物價市場。
明清時的痲瘋病患者的下場,通常不是淪落為社會邊緣人,就是被送入痲瘋院與社會隔離,這些患者大多受到家庭與社會的雙重排斥。 例如,在明代,患者大多收容在府縣官設的養濟院中,像萬曆《雷州府志》就記載,原本離城較近兼收孤苦老人及痲的養濟院,可能在士民抗議合居不妥與影響府城衛生環境的情況下,將老人與痲瘋患者分別遷移至不同處。 除了地方官設的養濟院外,根據《澳門紀略》紀載,大約在萬曆七年(1579)左右,澳門已有一所傳教士所創的痲瘋病院,專收痲瘋病患, 這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以西方醫療方式收容和隔離痲瘋病人的痲瘋院。直到清初,兩廣地區才又出現官設的痲瘋院,如康熙時人屈大均《廣東新語》〈瘋人〉一文中記有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地方官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然後挑選其中一名患者為首領,禁止患者外出,這樣的隔離措施降低了痲瘋病的病例。 雍正時,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在離縣城十餘里的紅山地區,設有「癩民所」,內共收容癩民六十五名,一年政府約支出柴布銀三十九兩六錢五分,遇有閏月,則加銀一兩,後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縣劉業勤重修。 又民國《東莞縣志》記有,廣州府東莞縣原有兩座養濟院,其中一所建於南城外的花園嶺,專門收容痲瘋病患及盲人,病患中共有一百八十位痲瘋病患,每名每日給口糧銀一分,後知縣李思沆又另擇地增置兩所,共收癩民一百七十五位,每名每季給口糧銀四錢五分七釐。
清代雖然出現專門收容痲瘋的痲瘋院,但如同明代的養濟院一樣,部分設於城內的痲瘋院依然無法擺脫其連帶而來的治安與傳染問題。康熙《新會縣志》則提到貧子院內養瘋癩惡疾之人,位置靠近養濟院,後因癩兒行劫,乃焚其院,遷城西郭下,但又因該處靠近城邊水源地,每逢大雨就穢物四散,民眾因此染上痲瘋。
此外,尚有設於城外,禁止患者私自入城的官辦痲瘋院, 。廣東地方官對痲瘋院的管理似乎只在生活上給予口糧而已,實際上握有管理大權的是痲瘋患者中「痲瘋頭」,當地習稱「亞胡」, 這些痲瘋病者在亞胡的帶領下,每當地方饒富人家有吉凶之事,就會登門索錢,索食少則叫罵,唯有事先賄詻亞胡,才能免其痲瘋屬下的騷擾。 痲瘋院無異是個小型的自給自足團體,除了共有一位首領外,院肉亦常自為婚匹,生兒育女,偶有登徒子進來偷腥,瘋女一經「過癩」,往往宿病遠離後就翩然出院。 《蟲鳴漫錄》亦記有粵東省會及潮郡均有痲瘋院,凡男女得是疾者,軛送院中,自相匹偶,所生子女無異常人。 廣東痲瘋患者除了部分被隔離在痲瘋院外,尚有許多是獨居在外者。例如有些家庭會將家中患痲瘋者,安置於備有衣糧的小舟上,使之浮游海上。還有的會使患者獨居空曠之所。 此外,還有一些患者會淪於從事不法勾當的社會邊緣人,例如山寇或海賊綁票的取款人、州縣有司的鄉間催糧者、盜賊耳目、或者是乞丐。
綜上所言,無論是癩民所、或者是痲瘋院,大多是由地方官所設置。官設痲瘋院所能提供的只是痲瘋患者居所與每日口糧,毫無任何醫療可言,這樣的措施,多少只能算是收容所,到了清末,廣東各痲瘋院的管理方式依然無多大改善。史學大師陳垣早年曾治醫學史,寫過許多與疾病預防、治療相關的短文, 〈送鄭學士之白耳根萬國痲瘋會序〉一文提到,中國舊有的痲瘋院與候死所沒兩樣;除了少數傳教士所辦的痲瘋療養所外,未曾有過兼具隔離與醫療功能的西式痲瘋院。
結語
性、傳染、蟲、蛇、毒、痲瘋女與過癩似乎是明清社會對麻瘋病的共同的社會想像。據梁其姿的研究,這可能與受了楊梅瘡(梅毒)傳入中國兩廣一帶的影響有關。我們透過《解圍元藪》可看出其中端倪,沈之問將癩病與楊梅瘡混為一談,並且舉出閩粵地區的過癩習俗,可能加重了當時醫界與社會對麻瘋病的誤解。 此外為何明清時期的嶺南地區會被認為因特殊的地理環境與體質而特別容易感染到痲瘋病?事實上,明清之前不乏北方的大風/癘/癩病患者,但由於主流的南方醫者的社會想像與觀察偏差,使得楊梅瘡在閩粵一帶的肆虐影響了這種地理差異的想像。另一個可能是當時醫家大多南方人,所以目光大多集中在南方的風土病,而無視北方的情況。
明清時期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中,無疑地,過癩是小說作者目光聚集的焦點。痲瘋病在明清時期與性、蟲、毒與過癩等形象相結合,一改中古時期痲瘋病給人不道德的宗教意象。明清的醫者或社會大眾似乎相信痲瘋病的性格類型的存在――得痲瘋病與淫蕩的性有關。儘管痲瘋病被認為不只是可怕的病也是醜陋的病,但與痲瘋病相關的過癩文本卻美化了痲瘋女的形像;相對而言,登徒子或尋芳客的形像被描述為逞一時之樂的好色之徒,在這些文本中痲瘋病如同十九世紀西方的梅毒一樣――似乎訴說著痲瘋病是對不正常的性的懲罰。如同當代許多人相信癌症性格類型的存在一樣,現代癌症神話易將癌症患者想像成無感情、抑制與壓抑的人。如果我們難以想像痲瘋病的真實面貌為何能夠如此荒謬地被轉化,我們不妨考慮二十世紀另一惡名昭彰的病――AIDS。透過小說的訊息傳播,嶺南地區的過癩想像成了全國皆知的痲瘋病形象,這種熟知,不只是觀念上,而且反映在日常生活慣習上。換言之,小說在過癩習俗的傳播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關於這點,我們若從不同時期的賣瘋女的版本作一詳細的比對,似乎可以發現彼此之間無論在結構、內容或痲瘋想像上都相當類似,並且前後有相互參照與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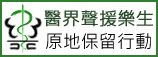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