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
三十多年前來自奧地利的谷寒松神父,以天主之愛的名,從六零年代開始,把自己奉獻給樂生院的癩病病患。這真是相當的感人,就像六七十年前,加拿大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戴仁壽宣教師&醫師,不但也是多年來奉獻給北台灣的癩病病患,還親手打造了台灣幾乎是最早的癩病專門醫院與療養院:樂山園。而戴仁壽如果今天在天上知道此事,他當然會反對拆除樂生院,因為他知道這樣一個建築物,在台灣近代醫學史、宣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不論如何,今天台灣關於樂生院拆除與否的爭議,其實已經超越了神父或宣教師是否終身奉獻給癩病病患的問題。
在谷神父自己的投書中,重點是樂生院的院民。癩病和病患,不管他們住在哪裡,重要的是他們是否受到不錯的照顧。如果有,就該心存感謝,而不應該缺乏感恩的心靈,以致被「有心人士」利用。
不過,樂生院的院民,無論就客觀的歷史或主觀的身心,其實和樂生院本身是很難分的開的。
我們知道,日治時代的樂生院,是台灣殖民醫療時代特別的產物。它對院民與社會上疑似有癩病的人,都是先作強制性的拘提,然後作強制性的隔離。這些強制作法的目的,主要是台灣總督府的面子問題,為的是避免在日本統治的近代殖民街頭上,看到流浪的癩病病患,而不是基於當時對癩病的醫學研究,認為有需要絕對的強制隔離(當時有很多爭議,而且常有醫師以門診的方式來治療癩病)。許多院民,當初在被拘提之後,就和自己的家庭生離死別,被關進一個被嚴格監控與規訓的空間。所以,這座樂生院及其台灣殖民醫學的歷史,正是台灣日治時代的一個重要的象徵,透過它,我們才更能理解我們的父祖之輩,還有他們的身體,在日治時代,是怎麼在面對殖民權威、是怎麼樣的被監控與規訓的。
所以,即使今天所有樂生院的院民,都願意遷往迴龍社區,樂生院還是不應該拆。它是台灣人民的古蹟、它也是台灣醫療史的重要見證。更何況,在戰後台灣,雖然癩病已經有更好的治療法,不一定需要嚴格隔離,但是樂生院民已經逐漸與樂生院形成一體,他們反而不見得能重新適應這個社會,而我們的社會也不見得能夠開放心胸來接受他們。樂生院再經過一個歷史的翻轉,從嚴厲監控的場域,轉換為長年居住其中的院民的社會避風港。今天從日本到西方的許多地方,過去的癩病監控所,也都已經轉換為院民生活的新天地、新村莊,這種集歷史古蹟、記憶、生活新天地於一身的前─癩病院所,怎麼可能輕易的就被一所新的醫院所替代?
可貴的是,今天樂生院面臨拆遷,社會上有許許多多的朋友,既關心我們的老院民,也關心台灣歷史上的樂生院古蹟, 不求回報的來保護這段歷史中的人、事、物,谷神父怎麼可以懷疑這些人是有心人士在利用樂生院啊?谷神 父在樂生院三十年,照顧院民,藉以發揮天主的愛心,我們也沒有說谷神父是有心人士在利用甚麼啊?
最後,因為谷神父只關心院民,當衛生署提供新的去處,就應心存感謝,但卻不 太關心他居住三十多年的樂生院,所以,他對於捷運局「樂生必須拆遷、捷運無法改道」的說法,沒有提出任何的質疑。其實,我們台灣的工程界,常常自詡甚高,人定勝天的氣勢十分常見,雪山隧道可以不顧水源,斷然開鑿,說以後再解決水源問題,美麗的蘇花海岸也要開出高速公路,甚至如果因為是國家公園而不便開鑿,有工程師甚至說乾脆要開出沿蘇花海岸的海洋高速公路來。這種工程霸氣,碰到樂生院,卻黔驢技窮,卻說無法改道,誰能相信?最起碼,當初和衛生署平行的政府單位文建會,請來同樣專精於捷運專業的欣陸工程公司,研擬了90%樂生院原地保留的方案,為何谷神父就完全不提呢?
願我們以天主、耶穌、阿拉、佛陀、天尊、媽祖的愛心,保佑樂生院能夠長久存在,成為台灣歷史、醫學、工程、人權、倫理發展上的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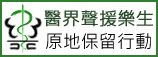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