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癩病日、反思台灣癩病患者的處境
從世界癩病日、反思台灣癩病患者的處境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副教授 范燕秋
(本文寫於2004/01,未刊槁)
全文轉載自樂生院人間寫實http://blog.roodo.com/losheng/archives/79940.html
「世界癩病日」(world leprosy day),一個國際公共衛生的節日,定在每年一月最後一個星期日,今年就是一月30日。這節日是1954年由法國慈善家佛樂豪(Raoul Follereau 1903-1977)律師發起而制定,其目的是希望世人認知癩病(俗稱:痲瘋病)是可以治癒的,消除過去恐懼和歧視癩病患者的現象,並呼籲人人都應該向他們伸出援手。許多國家在這一天舉行相關會議或祈禱活動,呼籲世人關懷癩病患者的處境。
在台灣,這樣的節日能提供我們社會何種省思?
台灣的癩患病友多數集中在台北縣新莊的「樂生療養院」,為數約三百人,平均年齡在70歲以上,他們多數是長期以「樂生院」為「家」,一群孤獨傷殘的老人。樂生院在1930年創設,也就是戰前、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不少患者竟然在這個院區居住達半個世紀以上,或者已經老死於院區;他們既無法返回自己的家鄉,也失去可以聯繫的家族。這究竟如何造成的?又存在何種孤苦無告的故事?
若推究其主要原因:癩病是人類很古老的一種疾病,西元前已發生於世界各地,聖經及論語都有關於癩病的紀錄。然而,它也是所有疾病之中、最被污名化的疾病。由於癩病很難被治癒,其發病的晚期患者外貌又產生極大改變,如眉毛脫落、鼻梁坍塌、指骨內縮等,造成醜陋的面貌、手足畸型以及嚴重殘障,這種疾病被視為「天刑病」,是上天的懲罰,或是一種遺傳病。因此,患者長期受到所處社會的歧視與排斥。
或許很多人認為十九世紀現代醫學發展之後,憑藉現代醫學的進步,很快可以挽救患者的悲運?事實並非如此,「樂生院的故事」是因此才開始的。近代醫學、特別是細菌學發展之後,初步能掌握癩病的病原體。1873年,挪威籍醫師韓生Dr. Armauer Hansen從癩病患者的喉頭、鼻粘膜及皮膚組織,發現癩桿菌(Mycobacterium Leprae),初步認定其為傳染疾病,也為近代式「癩病隔離」措施、提供了學理的依據。由於至二次大戰末期為止,癩病尚無良好的治療藥方,二十世紀前期多數歐美國家以及日本,基於「公共衛生」的考量,對癩患採取隔離療養的方式。
在台灣,隔離療養機構的設置是在日本治臺之後,因日本在台灣推展近代醫學與公共衛生而出現。比較具有意義的,是當時台灣的癩病處理存在教會醫療與殖民政府兩種系統的競爭,而且最早關切而從事癩病門診醫療的,是西方傳教士主導的教會醫療,原因是:救治痲瘋乃是基督徒自古以來體現博愛與救人濟世的重要事工。然而,能運用國家公權力全面管制癩患的,終究仍是殖民政府(台灣總督府)。
由於台灣總督府的施政是因應殖民政策的變動,日本本國在1907年制訂法令、建立癩病療養所,對癩病採取隔離措施;台灣則是始於1927年,興建全台唯一的癩療養所-「新莊樂生療養院」。1930年12月樂生院正式開辦,開始收容日、台籍癩患者(仍以台人佔多數)。1934年台灣總督府公布「癩預防法」,延用日本癩防治法規,加強強制隔離措施。因此,收容患者人數快速增加,至1939年達最高額之700人。
而樂生院故事的開端,也就是來自強制隔離措施。由於當時對於癩病醫療的侷限,凡被送進樂生院者,注定是被終生隔離的,因此患者與原來所屬的社會關係幾乎全然被斬斷。同時,由於衛生警察公然逮捕、監禁癩患,造成廣泛的社會恐懼氣氛,更加深社會對癩患及其家族的歧視與貶抑。這種措施在公共衛生的意義,是為維護公眾社會健康,不惜枉顧人權,以國家公權力監禁、限制癩患者的行動自由,同時也其負面的社會認知也進一步被強化。
另一種造成癩患者社會關係斷絕的狀況,是隔離機構對結婚患者施行的節育處理。由於癩病是慢性溫和的傳染病,很難傳染;癩桿菌也很難在實驗室培養出來,可說違反細菌學原則,因此醫學界對癩病的傳染與否存在一些爭論。而且癩病潛伏期長達數年或數十年,多數不了解是從何人或何時感染,因此又常被誤以為是體質遺傳。這些醫學界較難掌握的疾病特性,合理化國家對癩患者施行強制節育,不少患者遭受終生的身心傷害。
1945年日本統治結束,台灣歷經了政權轉移,癩患的處境似乎也有新的轉機
。特別是戰後癩病防治基於兩個時代因素,使其轉向新的里程碑:其一,1940年代中期抗癩特效藥、磺化藥物普羅敏(Promin)及戴普松Dapsone(DDS)的研發、使用,由於它們有效抑制癩桿菌,為癩患醫療帶來福音。由於1950年代DDS普遍使用,及1960年研發出能完全治癒癩病的Rifampicin與Clofazimine,國際間倡議新的防治措施,揚棄戰前強制隔離政策,鼓勵採取尊重人權的開放處理,以及門診治療方式。
第二個因素也就是1954年Follereau發起「世界癩病日」,所彰顯的時代意義。即如1956年國際會議決議的「羅馬宣言」,明確列舉具體措施,包括:撤廢差別待遇的各種法律,進行廣泛教育宣傳、除去社會偏見和差別,重視早期發現和治療,許可患者自宅治療,限制入院的規定,及提供人道、社會、醫學的援助,保護患者以及使其返回社會。就此觀之,佛樂豪顯然認知:除非發起廣泛的教育活動,喚醒世人對癩病的普遍認知與反省,否則不可能改變世人積習已久的、恐懼和歧視癩病的現象,也無法轉化癩患被社會孤立的處境。「癩病日」就是在戰後癩病醫療進步、防治措施更新的脈絡之下,為癩患者爭取符合新時代處遇的一種努力。
對於台灣而言,這些新時代的癩患處遇能否落實,面臨許多困難與問題。首先,由於戰後初期台灣政局的不穩定,以及另一波新移民的進入,使癩患的境遇處於混亂的過度期。當時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軍民之中,發現不少癩病患者,而樂生院仍是收容這些癩患的主要機構,收容人數最多時達三千餘人,其中區分為民患與軍患,並增設病室給軍患住院。
此外,對於戰前被強制隔離於樂生院的患者,雖然可能有機會返回家鄉,然而,不少人終究因「痲瘋」的污名,而被迫再度返回樂生院。也就是儘管抗癩醫療藥物進步了,但社會大眾對於癩病的的歧見並未消除,因此他們僅能退回到原來與社會隔絕的世界。就此,樂生院成為新、舊癩患者共同的家園。
同時,原有的不合情理的防治措施,也不見得能徹底修正。1950年代初由於美援的進入,臺灣的公共衛生開始與歐美國家接軌。因此,1952年之後臺灣引進、普遍運用普羅敏(Promin)及DDS,促進癩患醫療的進步。1962年,政府也修改癩防治法律,廢止強制收容,而採取開放門診方式,若有必要、仍可往樂生療養院住院。然而,對患者婚配時施行的節育措施,仍被延續了好一段時間。至1960年為止,樂生院院方仍強調:節育為癩病所必須。本院為管制病人之生育,對於在本院已結婚及將結婚之男女病人之一方,必須施行節育手術。(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三十年紀念特刊)這項醫學的偏執竟然並未隨醫藥的進步而被檢討、修正!
若從社會認知而非醫療的角度,從戰後、直到現在,樂生院院友仍然是被隔離、孤立的。從這個角度來看,Follereau提倡的「癩病日」的用心,也就更值得台灣社會省思。他呼籲世人認知癩病可以治癒,並提供各種援助,保護患者,使其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台灣社會何時、又如何養成這樣的思考與行動?
事實上,樂生院院友就是因長期被孤立於社會之外,1990年代行政當局在規劃新莊的交通建設之際,在最不費時、費力的情況下,直接被宰制、犧牲的還是樂生院。去年(2003)六、七月,樂生院已經因新莊線捷運工程被剷除大半院區,目前尚且留存的是1930年最早的、核心的主體建築。而2004年樂生院的命運又如何?
「新莊樂生療養院」-從戰前到戰後、新舊癩患病友的共同家園,見證台灣近代癩病防治的來龍去脈,也是臺灣近百年公共衛生發展的縮影。由於這個院區的存在,這些長期被台灣社會排斥的患者,尚存有一個避世的桃花源。在此,他們與癩病奮戰之餘,發揮殘而不廢的精神,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默默的貢獻台灣社會,這個院區迴盪著許多他們打造家園、貢獻社會的故事。
同時,作為一個近代式的傳染病隔離機構,它的建築空間彰顯著特定的意含,透過這種實體、具象的視覺空間,處處提醒著世人反思疾病與社會的關係,以及近代國家暴力與公共衛生的辯證關係。而在這樣的院區,現代醫療如何研究癩病、照顧患者,以及在克服難纏的癩桿菌留下所重要的醫療經驗,是台灣醫療史不可或缺的一頁,更是與國際公共衛生對話的議題。
台灣社會能否正視這樣珍貴的歷史文化資產,為當今社會以及後代子孫留下足供學習、警醒的實證?!我們國家行政當局是否有此眼界與魄力?台灣公共衛生與醫學界的領航人是否有此智慧?答案在茫茫的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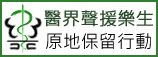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