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 新院區有比較差嗎?(4)「雙院區」提案
弱慢的另一篇文章:
新院區有比較差嗎? (4) 「雙院區」提案
俟獲得原作者同意之後會將部份文章放在這裡。
從醫界連署出發,醫療、公衛界共同守護樂生
[原文刊載於弱慢的部落閣,經作者同意後轉載。轉貼技巧拙劣,只能節錄部份,還請見諒。]
瘋癲,在人與事物的核心裡,是個反諷的符號,它錯置了真實與妄想之間的路標,僅成為巨大悲劇性徵兆的殘存記憶---是一種被擾亂多於擾亂的生活、一種社會中的荒謬性騷動、一種理性的橫流。
-----摘自傅柯《瘋癲與文明》第一章「愚人船」。
翻開樂生療養院的歷史,就是一部漢生病友被「正常」社會給驅除、監禁、隔離、污名、與敵視的血淚史。自1930年日本人草創「台灣總督府樂生院」至今,不論是殖民統治、極權統治、乃至於民主時代的當權者,從未認真地對待這群病友的真實需求。自發病的那一刻起,漢生病友被迫遠離家園,與父母、親戚、朋友永遠分離,上了樂生療養院這條與世隔離的「愚人船」,他們被迫結紮,實驗新藥,直到化作骨灰,也不能安葬家鄉。
時至今日,雖然新的醫療知識已經明白漢生疾病的來龍去脈,去污名化的工作也正在進行,然而,在空間上,我們依然承襲著過去錯誤的觀念,打造一條鋼筋混泥土的「愚人船」,迫使漢生病友再度與世隔離,放流到社會遺忘的角落。
這條新世代「愚人船」,就是樂生療養院的迴龍院區。
1994年,在台北市捷運局的強勢徵收與規劃下,(前)台灣省立衛生處不得不賣出樂生院區的土地,自此,新莊線的維修場、駐車廠與行政大樓就從原本的輔大後山,換到樂生療養院這塊山坡地上。從這一刻起,衛生署賣出的不只是一座山而已,還包括山裡老阿公阿嬤親手栽種的榕樹、破舊卻溫馨的木造房舍、不堪回首的歷史記憶、以及原地安享天年的最後希望。
現在,新莊線捷運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展開,70%的樂生療養院已於2002年毀於推土機下,面對來勢洶洶的工程大隊,樂生的老阿公阿嬤們最後的依靠,就是這孤立無援的30%殘破家園。
1994年,衛生署與捷運局達成「先建後拆、就近安置」的共識,希望在捷運機廠附近,興建新的療養院,以收容搬遷之後的漢生病友。衛生署原本承諾的是家庭套房式的低樓層建築,然而,在1999年迴龍院區開始規劃之後,政策卻做了大轉彎,原本低樓層的專屬院區,變成A、B兩棟相連的八層樓醫療大廈,一半做為樂生療養院、一半做為社區醫院,提供門診服務給當地居民。
再一次,衛生署為了經濟效益,賣出了對漢生病友的承諾,將原本低樓層的專屬院區,改變為高層樓的綜合醫院,枉顧病友的權益,也逼迫他們接受一棟完全不適合他們居住的水泥空調大樓。
至弱慢的blog繼續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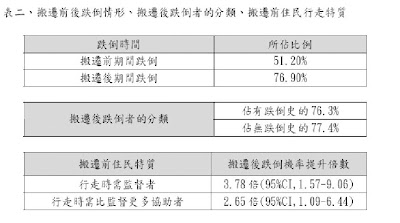
「軌」話連篇 阻礙樂生捷運雙贏
【聯合報/喻肇青/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劉可強/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2007.03.24 03:03 am
對於樂生爭議,昨日行政院終於釋出善意,蘇揆對於文建會所提出的百分之九十保存方案態度,指示工程會設法瞭解溝通,樂生保存問題終見一些轉圜餘地。
未料捷運局長常歧德卻跳出反對,表示「迴龍站體與線型軌道都已完工,除非拆掉已蓋好的迴龍站與線形軌道,否則兩個替代方案目前看來都不可行。」常局長又表示,保留樂生至少要花三十億。筆者見捷運局以顯見的謊言愚弄公眾,不禁憂心:捷運局若持續假專業技術之名欺瞞社會大眾,將阻礙保存與工程雙贏的可能。在此簡單指出兩點事實:
一、軌道根本尚未施工,替代方案也無須動到迴龍站體。
目前新莊機廠駐車廠與站體雖已完工,但軌道部分根本尚未施作,捷運局表示替代方案必須「拆除軌道」,我們想請常局長指出「已完成的軌道」在何處?而文建會的百分之九十替代方案,根本無須動到迴龍站站體,這是在專業的報告書中顯而易見的事實。捷運局在先前文建會所召集的數次會議中,也未曾提出關於拆除迴龍站體的說法。常局長這樣的說法是欺騙社會大眾,將使捷運工程專業失去公眾的信任。
二、從三百億到三十億,捷運局說法已成信口開河。
五年多前,台北縣古蹟學者會勘樂生提出保存建議,當時捷運局表示無論何種保存方案皆須「三百億」工程費,藉以嚇阻文化局進行古蹟審查;兩年多前,劉可強接受行政院委託提出樂生院全區保存與捷運機廠共構方案,當初捷運局的評估也是喊價「三十億」。而近日由欣陸工程顧問公司提出的評估報告中,保存百分之九十的方案僅增加工程費二點九億元,工期基本上不影響,幾次相關會議中,捷運局也未曾有過「三十億」的說法。然而,當行政院表示願意了解新方案時,捷運局長又立即高分貝地喊出「至少增加三十億經費」,不知這樣的說法有何專業憑據?請提出實際的數據。
捷運局每在樂生院保存關鍵時刻,以工程專業之名,恐嚇相關單位不得做出重要的政策決定(包括古蹟審議與替代方案的採行等)。五年來,捷運局使得樂生院保存決策的時機不斷延宕,造成爭議無法解決,如今真是「做賊的喊抓賊」。
以專業觀點言,樂生院要保存是「事在人為」。捷運局長期以來僅為圖工程之便的官僚心態,藉由壟斷公眾訊息,造成無謂對立,也讓社會承擔太多金錢、文化、環境與社會成本,造成了許多不可回復的傷害與損失。這樣的公共工程專業,不禁令人憂心台灣公共建設與環境的未來。
【2007/03/24 聯合報】@ http://udn.com/

黃文章
現居住於新生舍
高雄岡山人,71歲,民國25年(1936)生
民國44年入院
金馬數位影展紀錄片獎
「樂生活」主人翁
「…你們念醫學的,聽聽這些故事多了解不錯啊,這些故事讓大家知道,知道樂生院裡面的故事,是很好的。…」
生長環境
我覺得我生錯時代啦,也沒有去讀過書,日本時代時讀過一年左右的書,但是戰爭就來了,戰爭時也沒辦法念書,因為我們家就在機場旁邊,戰爭時很危險啊,就搬去山內住。等光復之後回去,大家生活都很苦,吃的都沒了,怎麼還能去讀書呢?中國政府來了以後,念書還要交六十塊的學費,怎麼交呢。我親生的家裡那邊有兩個兄長,我是給了人家的,之後還有兩個小妹。養父母這邊有兩個姊姊,我之後還有一個小弟,和一個小妹。
發病
我是十六歲的時候發病,皮膚紅紅的,肉就會麻,皮會整塊落下來,但都不會痛,裡面的肉青青黑黑的,手麻麻的,去檢查,醫生即使不知道我的手會麻,但看到皮膚一塊一塊紅紅的樣子,就知道是痲瘋病。
那時候我也沒聽說過痲瘋病,也沒有聽說過什麼醫院,回家以後,就開始吃藥,找漢(中)醫,鄉下漢醫給的就是一些青草藥,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藥,有吃的、有擦抹的,也有拿來洗身體的,人家介紹,我就吃,吃了很多種,最後還吃到一些味道嗆到吃不下去的草藥都有,還要先用滾水燙過,難吃到後來一吃就吐出來,吃得很痛苦,但是這些藥也都沒效。
那時也注射penicillin,和一種叫606的藥,他們說606給小孩子注射不好,我就沒有注射了。大風子油我沒有用過,我來樂生的時候已經沒有大風子油了。注射penicillin之後病稍微好起來,但我也還是照樣去做工,生活不好的時候,生病也還是要工作啊。到後來臉上也是,到處一直耗(害)下去,外貌難看了,都不敢出去,一直在厝內。到了最後,也都沒有朋友了,大家都怨尤我,怕會傳染,那時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大家一起出去玩,都不敢找我。我要出門的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多孤獨呢…即使出去了,因為難看的關係,頭也不敢抬起來,把帽子壓得低低的,到了最後,二十歲的時候,衛生所就把我抓來了。
所以我是從十六歲開始發病,稍微好一點一段時間去做工,病又再度發作也一段時間,到了二十歲時進來的。
我們家鄉那邊,除了我還有一個也是痲瘋病的患者,大概四五十歲,他的病很重了,都在家裡,在發現我自己得病之前,都不知道他得這個病。我是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但是大人也從來沒有提過,很奇怪。後來我發現得病,衛生所的人跟我說他也是痲瘋病,後來聽說要被抓來這裡,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恐懼,自殺了。
至於到底是為什麼會得到痲瘋病,我也不知道,一直覺得很好奇,但是痲瘋專家的醫生很少,只有以前有一位日本的犀川醫生,其它就很少了。
入院
我是民國44年入院的,現在已經民國90多年啦,我住在樂生已經五十多年了,也是不簡單哪。是政府強制收容,把我抓來的,那時候在南部我們都說,來這裡是來討死,村裡的另一位患者還自殺了。傳說到了樂生裡面就把病人給毒死,因為日本時代入院的人都沒有回家的,所以大家就傳說他們被毒死。我剛來樂生那個時候,也不准回家。和我同時一起被抓來的有四個,之前有六個人逃跑了,我本來也不願意來,也差點想要逃跑,但是衛生所的人在家裡等著,我們就這樣被載來了。先用車子把我載去高雄的一間醫院,住了一晚之後,天亮再載我們去火車站,由兩個衛生所的人押著四個病人,車子外面還貼著紅單子,寫著「痲瘋專車」,當時有學生也想上同一節車廂,衛生所的人叫他們看看外面貼的字樣,他們看了以後,還往裡面好奇地看看我們。火車到了桃園之後,就換了三輪車載我們,我們坐的車子都用消毒水消毒,剛好三輛三輪車,一輛坐兩個人,那兩個衛生所的人就坐同一台,一路上都是石頭路,很不好坐,到了樂生的時候,我和另一個也是二十歲的患者,還要幫忙另外兩個五六十歲,年紀大的患者下車,走到大禮堂那邊。一些原本就在裡面的患者就在大禮堂前面,問我們一些問題,「你哪裡人?哪裡來的?」我說我是鳳山人,一樣是鳳山的患者,就把我帶進去找地方住。那時候是陳宗鎣院長,他並不願意我們出去,就先抽血檢查有沒有菌,確定是患者之後,就留下來。
剛來的時候,房子內都住滿了患者,沒有地方住,我就住在屋簷下面,一開始是跟著一個鳳山人住在平安舍那邊,幸好是夏天,不會太冷,後來屋內有人過世了,我才搬進去屋內住。當時樂生大概有上千人,男女夫妻也有一起住的,但如果是夫妻就會有個隔間隔開,單身的就一張床這樣睡,本來就這樣隨便住,後來才蓋了貞德舍給單身的女生住。
院內生活
以前有管制不准進出啊,從大門進來的地方,有警察也有憲兵在顧,如果偷跑出去就要關緊閉,不能出去。
是在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還是很嚴格,我們只能在裡面生活,不能出去社會上,樂生裡面就有市場,豬肉店也有兩間,豬肉、菜是從桃園載回來賣的,菜市場現在也還有啊,就在貞德舍那邊。民國四、五十年的時候,開放以後,就改變很多了,外人也可以進來,我們也可以出去賺錢工作了。開放可能是在DDS之後了,可能因為日本的犀川醫生來了以後,認為這個病可以出去,陳宗鎣院長就開放了。
我家裡面的人也沒有來看過我,因為地方遠,交通不方便,而且古早時代的人,也不識字沒讀冊,我是來了一兩年之後,自己有偷偷的回去南部看。那時候回南部多艱苦啊,在火車上也是頭低低的,一隻手遮在臉旁,就怕被人發現,如果被人發現會被抓回來啊,怕都怕死了,那隻手就這樣一路上都撐著,不敢放下來,整趟路下來痠疼得不得了。我就是這樣一路坐回鳳山去,說起來這個病真是很冤枉,政府這樣子抓…唉。
我來樂生的時候,小弟都還沒讀到國民學校,後來是小弟在當兵的時候,有來看過我。我後來也一年回去好幾次看哥哥,但也不好意思,因為哥哥都叫他的兒孫來載我,我回去一次,他們就要塞車四趟路,心裡過意不去,就跟他們說,我要回去自己回去就好了。後來這幾年哥哥過世,就沒什麼回去了。
我在樂生院內沒有做過粗重的工作,但是做過的工作很多種。做過買賣,有賣過果子、賣菜,去外面的市場拿貨載進來賣。也有養兔子,買了養來賣人吃的,養在山頂,那時候樂生很多人在養兔子,因為要賺錢啊,菜錢不夠,才一塊三角半,太少了,只能配塊豆腐,營養很差。養兔子很趣味喔,兔子很會生,養一個月就會生小兔子了,一生一窩就六七隻左右,多的時候還有十幾隻的,養差不多一個月,就可以騎腳踏車載出去賣了,騎到台北市北門口那附近,有人就在那邊買賣兔子。兔子蹦蹦跳的樣子,還有眼睛也很可愛,啊,真的很有趣。大概在二十年前左右吧,兔子還大漲價,一隻幾百塊,大隻的還有上千元的,因為有一些生意人投機炒作,變得價錢很貴。樂生裡面也有人養雞的,後來也有人養博美狗,養的好的一隻可以賣五千塊。賺這些錢也就是來加菜啊,那些發的錢是絕對不夠的,不打拼、不工作,也是不行。
以前的錢很大,吃公炊的話一個月要交的錢是一個人五塊,十個人五十塊,可見那時候錢有多大。像掃地、打掃環境這些工作,也都是患者自己出錢請人來打掃,比如一棟房子住了三十個人,就一人出一塊,大家一起出錢請人。我來的時候都是吃公炊,到後來就可以自己煮了,現在我也是自己煮,沒有再吃公炊了。
(阿正伯伯補充)大概民國三十九年的時候,以前樂生院內還有請人來唱歌仔戲,就在大禮堂,外面的人也可以看,要買票看,但是中間再拉一個草繩,一邊是外面的人,一邊是病患。不過那時我還沒進來。
病症
剛來的時候我的手腳都像你們一樣,是好好的,但是痛發作的時候實在痛苦,手的筋骨會痛,痛到都蜷起來、四肢都歪曲了,也痛到整晚都睡不著,很多人痛到受不了,比較沒有勇氣的,都去自殺了。自殺的人很多啊,樹上都吊了很多,我剛來的時候聽人家講有一個自殺了,還跑去看,看了以後嚇到了,晚上還睡不著覺呢。
那個痛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好的,一痛就是幾十天,藥吃了也只是止痛用的,有時間性的,藥效若是過了之後還是會痛。如果沒有睡好,或是感冒,身體比較虛弱的時候,就會特別容易痛,外傷也會特別嚴重起來。
我的鼻子是來了樂生之後沒有多久,因為會塞,會流一些東西,塞住鼻子,不能呼吸,不舒服就一直去擤、去挖,弄久了就破了,還會流血,到後來也沒感覺了,久了就壞了。
我看了很多病人,剛來的時候都是皮膚一蕊一蕊紅紅的,厚厚的,有點高高的那樣,很難看就是了。發作的時候還會更腫一些,像一丸一丸腫起來的。
我來時民國44年,是一個禮拜吃兩次DDS,一次吃一粒。
止痛藥只能暫時止痛,但是即使是DDS對於神經痛還是沒有效,吃了還是會痛,而且越吃會越痛,而且DDS吃了會「破血」(溶血),紅血球、白血球會被破壞,如果身體不好的時候吃,會很痛很不舒服,若是身體比較勇健的時候吃,比較不會痛。而且虛弱時吃DDS,人會比較”sen7”,就是頭殼會變得笨笨的,眩暈。吃了藥,破血、暈不舒服的時候,飲食就要吃得比較營養一點,把身體狀況養好一點,會比較好。
以前如果把藥拿回來,不吃就放著,那就是準備要自殺的,一次吞大量下去,就死了。也有上吊自殺的。病痛,就是這麼苦啊。
醫院院方沒有給我們什麼特殊的治療,應該要這樣說啊,他們把我們強制收容來這裡,目的並不是要治療什麼,而是要把我們集中起來,隔離在這裡而已…是這樣的。
以前吃的DDS藥劑量比較強,現在的藥量比較薄了,他們有說是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再吃一下,但我想現在年紀都這麼老了,也都快死啦,還吃藥做什麼,就沒吃了。現在去跟醫生討,他就會開藥,一次開三十顆,一個月的量,或是你要慢慢吃吃更久也可以。
現在也不同了,還有一種吃了肉都會變黑的「黑藥仔」,就是B663(由阿正伯伯補充),我覺得吃了以後真正有效,真的有用。這是我自己觀察的經驗,尤其是一些比較後來發病的人,都是吃這個藥。像是手上皮膚那些一蕊一蕊都紅紅的斑疹部位,吃了藥以後都會烏黑,皮紅烏紅烏的,但是繼續吃下去,要吃一整年喔,但吃完了以後,藥停了一陣子,顏色就會退去,變回肉色那樣,就好了。我現在是沒吃啦,但還有人在吃,而且這個藥吃了以後肚子會很餓,想吃很多東西。一些會暈暈的副作用多少還是有吧,但現在生活比較富裕,營養較好,身體比較健康就比較不會不舒服了。
如果我以前發病的時候就有這種黑藥仔,就太好了。
現況
現在我也不怕人家看了,年輕的時候,自尊心比較重,很怕別人看,覺得自己的面目不好看,頭都低低的,也很傷心。但現在老啦,也沒什麼好怕啦。至於什麼時候開始不會怕人呢,我自己的感覺是,要感謝輔大的學生。也很久了,三十年前開始,他們都會帶我們出去玩,一年一兩次,每次遊覽車六七台啊,我想大概是有募款吧,台北也去,最遠還去到台中港,也有遊樂園、小人國,宜蘭冬山河等等,那些自卑感就沒了。還有去台北市錢櫃訂位唱歌,我很愛唱歌的。樂生那卡西的CD我也有錄,賣得還好嗎?有銷吧?有銷就好了。馨文琬純他們很打拼的在賣喔。
現在身體的一些不舒服,就是筋骨痠痛,手也會,但可能是因為年老,而不是因為痲瘋了。
你們念醫學的,聽聽這些故事多了解不錯啊,這些故事讓大家知道,知道樂生院裡面的故事,是很好的。
樂生口述歷史工作坊 馨頤整理
轉貼自http://diary.blog.yam.com/honkwun/article/3054247
全生園的燈火
我常在禮拜天的時候散步。走一走大概不要兩三個小時的時間,就可以有遠離工作的感覺;哪怕只走個三十分鐘,也能把心思放空,然後隔天又神清氣爽地繼續回到桌子上工作。一個禮拜要是都不走路,便覺得又漫長又沉重;如果能稍微去散個步,就能持續工作下去。在我散步會經過的地方當中,有一道柊樹所生的樹籬,位在國立漢生病(俗稱麻瘋病)療養院──多摩全生園那裡。現在全生園的門戶是開放的,而且樹籬有被修剪過,矮矮的很平易近人;可是之前我一直猶豫著到底要不要進去看看。我對漢生病的了解已經跟常人差不多了,它感染力弱,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只是政府的隔離政策讓偏見與恐慌深植人心,對根絕這種疾病毫無幫助,沒有任何助益可言。但我並沒有好好反省、覺悟,想想自己是否擁有直視這片樹籬之後的資格;純粹因為好奇而想走進去看看,這點說實在很不禮貌。我第一次走進全生園是在魔法公主最忙的時候。那時工作很重,又沒進展,就算散步也還是間歇性地感到不安,心想不把原地打轉的腦袋給靜一靜是不行的。就在這麼煩擾的時候,好像有某個契機指引我;在初春的慵懶午後,我突然想走到樹籬之後看看。一開始吸引我目光的,是並排的兩行巨大櫻樹。眼前被夕陽染黃的枝幹閃耀著光芒,樹梢上的枝芽往高高的天空伸展。
這是怎麼樣的一股生命力啊,我被震攝了。有種幾近於畏懼的情感困住了我,結果那天我就這樣回去了。過了一個禮拜我再到全生園去,心情依然畏懼,連資料館那裡我都是屏息而入,但卻有意料之外的收穫。沉默之中,漢生病以及要面對它的人們的紀錄,一字一句地攤在我們眼前;其中有著人類最為高貴的情操,也有社會最愚蠢的一面。
看到這些紀錄,與其說被走過這段歷史的人們所打動,不如說內心被他們生存的樣貌留下了印記──在這般苦難之中,他們卻能不忘歡喜和笑容。對渾渾噩噩的眾生來說,恐怕沒有像全生園這樣,可以把超脫苦難的生命看得透徹的地方了。
(我感到:)不能草率地活下去。
就像其他經由長者的教誨、體悟到這個道理的年輕人一樣,我的心情在看過資料之後坦率了起來,然後走出了資料館。從此之後,全生園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禮拜天散步的時候,我開始走到園裡面去。園裡總是又乾淨又安靜,裡面的人也都溫和有禮。有時參觀的訪客蠻吵雜的,我總狐疑地想,他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傲慢了些。
在園內的一角,留著許多不再使用的建築物,包括病患本身的宿舍、被帶離病患身邊的小孩住的地方,或者在北条民雄的和歌──「望鄉歌」中的中小學分校,以及圖書館。這些病患生活過的地方,照理說應該充滿著悔恨和悲哀的氛圍,卻也沒有一點可怕的感覺;站在這裡,只覺得有種嚴肅的、溫暖的心緒湧上心頭。不管看哪一棟建築,都有這種正面的感觸。
我想,這些從昭和時代初期建好的這些建築,都保存地相當好。同時代的建築,在東京幾乎看不到了。聽說這些都是病友當中的工匠所建造的,就連用石頭鋪設的道路,也都是為了受泥濘所苦的人辛苦做的,是大家齊心協力才鋪好的。能保存這些建築,實在是件好事。不管就公衛史或建築史來說,它們都具有很深刻的意義。每當深夜的時候,在從工作地點回家的路上,我都可以從柊樹形成的樹籬中間,看到全生園的燈火。為此我常感覺到一種深深的懷舊之情;就像電影散場時,自己覺得當下身在一處聖地一般。現在日本政府好不容易對這些病患認了錯、謝罪,能這樣真的很好。我忽然想到,在日本各地,除了病患本身之外,包括他們的親人、子女和朋友在至親被強行隔離的情況下,仍須沉默以對之時──那私下偷偷落淚的情景。
宮崎 駿/著名動畫導演 日本漢生病大使
「全生園の灯」:朝日新聞:2002年4月20日朝刊譯自:http://www.hikoboshi.com/eba/inori/inori103MiyazakiHayao.htm
註:http://www.dwc.doshisha.ac.jp/campus_info/chapel/chapel130/01.html
據日本同志社女子大學的網頁說,神隱少女的場景就是宮崎駿時常去散步的全生園。神隱少女裡變成豬的父母(跟其他人),就是過去漢生病患的遭遇;他們過去不被當成人看待,被稱作「坐著的豬」(暫譯;或者譯作豬妖)。失去了在社會生存的權利,宛如到了死後的世界(隧道另一端的世界)。其他諸如強迫勞動、失去真名等等設定,也是當時漢生病患的生活狀況。其他地方看到的留言也有相同的意見。另外,動畫龍貓的靈感來源來自多摩本地;全生園裡還有一間宮崎駿出錢維護龍貓トトロ房屋(山吹舍)。
生長背景
我的名字叫林卻,我是民國九年出生的,我本來住宜蘭。小時候我們鄉下的種田人家,也沒有去上學。以前的人不知道節育,都生比較多小孩,我媽媽就生了八個小孩,女兒都給人,留下四個兒子。我排行第六,下面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四歲我媽就把我給我先生他們家當童養媳了,十七歲嫁去。我養母自己沒有生,四個小孩,三個女孩一個男孩都是別人給的。四歲雖然小,但也已經會做事了。
我十七歲時嫁人,十八歲時生一個女孩,現在都七十歲了。二十一歲時又生了一個男孩,現在兒子女兒都做阿公、阿嬤了,孩輩也好幾個了。照片裡的人是我的孫女,我媳婦生了五個女兒,都長大嫁人了。過年時有十個兒孫一起坐車來看我。
症狀、入院經過
我十四歲開始,還沒出嫁時左手就會痛了,是痛在「筋」,皮膚都好好的。慢慢越來越痛,手指也捲起來了,那時候就吃了三年的漢藥,但也沒什麼用,手還是沒有直回來。但到了十七歲年尾的時候我媽媽要我嫁過去,不嫁也不行,洗衣、煮飯也都是我做,結婚以後就沒有再吃藥了。這個痛,痛了一世人,雖然現在看起來皮膚好好的,痛的時候是痛入骨頭裡面的。
病比較嚴重的時候,皮膚會有紅紅的紅疹,厚厚的,一塊一塊起泡,發起來的時候整個麻掉,都不會痛,但好肉正常的地方早就痛得不得了了。身體也有,臉上也有。皮膚還會膨(腫)起來,破孔流一些黑血,非常痛,我的腳就是這樣,本來還不注意,後來整個腫得很紅很大,痛得要死。一些傷口,就是自己抹藥,日本時代沒有藥膏,就擦一些藥水消炎,像是這些藥水。一些傷口後來吃了DDS就好了,但是腳還是會破孔那樣,要擦一些藥水,嚴重的時候還會腫到膝蓋,整個腫的很不舒服,抬高可以好一點。
光復之後五六年,DDS發明了,吃多了也是有人死掉。吃了DDS之後肉會比較白,也比較有效,我是三十歲的時候開始吃,會畏寒、發燒,很不舒服。另一種「黑藥」是後來才有的,我沒吃過,聽說吃了以後皮都會黑黑的,像黑人一樣黑。
你們要問我過去的事,過去生活很苦啊,我二十一歲就來了,生完兒子沒幾個月就來了,本來都是看漢醫(中醫),後來去看了西醫,他看到我的手指蜷曲起(khu2-khu2)來,就知道是痲瘋病了。就向日本人報告,報警察,要我來這裡。日本人很嚴,不來也不行,他們說台北有醫院,有專門的藥可以吃,叫我來。以前我也沒聽過樂生院這個地方,鄰里間也沒有聽過有得這病的人,只有我而已。
我問他們藥要吃多久才會好?他們說要吃三年,我覺得三年實在太久了,台北離宜蘭又那麼遠,我不願意,但是台北和宜蘭那邊的醫生有聯絡,不願意也得來。警察去家裡通知,我丈夫和我阿兄就帶我來了。我們是坐火車來,一在火車上就有看到其它的患者了,一節車廂就坐我們六個患者而已,患者不能和其它人一起坐。坐到了台北車站下車,用垃圾車一樣的車載我們,沒有座位。以前是強制收容,到處去收,下港也有,宜蘭也有,有西醫和警察一起去。到了樂生來,也抽血檢查細菌。直到現在還是每年抽血檢查一次,看看有沒有細菌。我檢查出有病的時候,家裡的人和我兩個小孩,也都要去檢查有沒有病。
剛到樂生的時候,就分配我住進病棟,我就這樣進來了。
院中生活
家裡的人沒有來看過我,都是我回去,年輕的時候,面好好的,髮也好好的,鼻子、嘴五官都好好的,可以自己回去。有一次我母親寫信給我,說我丈夫把兩間厝都賣了,女兒也給了別人,雖然隔離,不能自由出入,但家裡發生重大的事情,指導員看了信,也准許我回家,請假一個禮拜,再長也不太行,我那時一個禮拜後還有事,就再寫信回來再請一個禮拜的假。
以前如果要回宜蘭去,要去樹林坐火車,三點就要起來走路過去,即使是有車也沒有辦法坐。戰爭的時候,還要趁晚上的時候走,因為戰爭,路上也會有伴一起照應一起走。太平的時候,就找不到什麼伴了,因為大家都怕這個病,聽說會傳染,面目也都不好看了。家裡的人看我從小到大,習慣當然不會怕。
剛來的時候,多艱苦、多歹命啊,沒有藥可以吃,天天都一直哭。剛開始的時候是手會痛,痛久了就麻了,那時候也沒有DDS可以吃,只有神經痛有些止痛藥,像阿斯匹靈,痛的受不了的時候就去注射,會稍好一點,但是仍然會痛。我剛來這裡的時候,左手痛,甚至痛到會抽筋,痛起來的時候,像在抽、一陣一陣,很痛的時候都痛到睡不著,這一痛就痛了十六年,直到有藥可以吃為止。日本時代很多人都痛到自殺,很多人都去上吊,吊阿嬤,哈哈。剛來時左手的手指是蜷起來的,但右手都還好好的,可以做很多工作,我也會做很多工作。日本時代是注射大風子油,也沒有什麼用,沒有藥可以吃,只有止痛藥。手指就一直一直壞了,像是提滾水的時候,碰到熱鍋的時候,就燙傷了,現在皮膚也都是死肉了,沒有感覺,冷熱也不知道,所以腳上也是會有很多傷。壞到有DDS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再讓手指頭生出來了。日本時代,院內的醫生護士日本人比較多,台灣人比較少,指導員也有台灣人的。因為怕痲瘋病會傳染,宣傳得很厲害,護士都摀著嘴,躲的遠遠的。
日本時代有很多人在樂生,我問其它的患者有多少人,他們說有七八百人。也有日本的患者,他們住在台南寮那邊的日本房子,一些他們習慣的有舖榻榻米房子。對於我們和日本的患者有沒有差別,我也不知道。
以前院內東西不夠吃,很多人都餓死了,尤其是年輕一些的人,胃口較好,常常都是肚子餓,生活很辛苦,錢都不夠買菜。以前這裡也沒有米可以買,我都是回宜蘭拿米來煮,日本時代米禁止買賣,有一定的配額。日據時代的公炊也都是患者自己煮,像我這樣病較輕,手腳還好好的輪流做。日本時代比較嚴,外面的人不能進來。要買菜也都要自己買、抬回來,也沒有工友可以幫忙,打掃也都是自己來。
戰爭的時候,生活更苦了,能吃的很少,常常就一碗飯配一些鹽,沒什麼菜,就這樣吃,戰爭時也不能買米,很多老一點的人也沒地方拿米,很多人就餓死了。死了的人就有竹子拼拼的架子,抬去山頂上,放平以後放一些草,點枝火柴,就這樣患者自己燒。聽說有一天死兩個人的,七八百人死了只剩三四百人。也有很多人逃走,再被抓回來的。
光復後日本的醫生護士都回去日本了,患者也一起回去了。有一些台灣醫生和護士再進來,有一個陳醫生就在日本的院長走後當了院長了。
光復後二二八的時候,米有比較夠,飯有比較大碗,吃得比較飽一點。但是光復後物價一直漲,一個月的菜錢也只有十二塊,一天四角錢,四角錢也只能買一斤空心菜,也還是吃不飽。
我年輕的時候,一屋子住的四五個人,年紀都比較大,我就一個人做四五個人的事,或是做些手工,賺三塊錢,即使錢不多,有工作我就去做。現在一塊錢掉在地上連小孩子都不要撿了。像以前的竹仔寮那邊,我也去做過工作,工作時拿一些冷熱水等等,手都會受傷。日本時代時不能出入,也沒辦法在外面買賣。如果有親友要來探望,也都要穿隔離衣、消毒衣,過消毒池。
我是在民國四十七年的時候搬進貞德舍來的,以前一間住十七個人,兩大間房間就三十四人,都是女生。一個三尺寬的眠床和一個櫃子,就是一個人的位子,也沒有電視、冰箱、電扇什麼的,是後來慢慢人少了,空間也寬廣了,才慢慢自己買了電視、電鍋的。每一個位子都有一個電表,每個月有六度的額度,如果超過就自己再貼錢。從日本時代就分配了一人一張床,和棉被,五年換一次新的。其它的東西、毯子也都是自己買的。水也有規定,一個月四度,不夠也是要貼錢,我以前手比較好的時候衣服也都是自己洗,不太會超過四度,這幾年才用洗衣機洗,比較耗水。
現在
現在公炊煮來的菜,有的都硬硬的,現在沒有什麼牙齒了,都沒辦法吃。便當就是包給外面的人煮,交兩千塊(一千八百八十元)給他們,一天三餐煮什麼菜就大家一起吃,工友再送來我這邊。如果有些比較軟的菜像菜瓜什麼的,我才比較能吃。
身上這件衣服是三百塊,我捨不得買,是同舍的一位阿婆過世以後,我才拿來穿的。電視則是託院民幫忙買的。
這幾年我有心臟病,不是痛,而是會全身無力,流冷汗、流眼淚,一直喘。發作的時候必須去住院。我就吃一些買的藥,孫子和孫女買了三百粒四千元的救心藥(中藥)給我,不舒服的時候就吃一粒,吃了以後就比較好了。
補充:
(張文賓,陳再添)
林卻阿嬤和院民葉學文是知己好友,晚年一起住在貞德舍,葉學文是第一個榮民院民,在二二八之前就入院了,當時外省藉院民不到五個。葉學文擅長書法、公文等,「以院作家,大德曰生」就是葉學文題的,過年時還曾自己作春聯寫在貞德舍,「淡飯清湯能飽肚,茅籬竹舍好安身」。
阿嬤每天早晚定期餵三隻貓,三隻貓也生了小貓,常常在貞德舍外睡覺晒太陽。
樂生口述歷史工作坊 馨頤整理
日本國立漢生病療養所~全生園見學經驗 序
2006 夏天 我到日本日本國立漢生病療養所全生園走了一回 2007.3樂生療養院保存面臨危機 正反兩方針對不同議題吵翻天 其中關於適合院民居住的空間議題的部分大多是各說各話表述
到底是新穎的機構式建築適合阿伯吹冷氣下棋,還是社區形式舊院區的三合院適合阿嬷拈花惹草; 我在全生園的所見所聞 也許可以作為另一種想像與可能
正當大家爭論不休之際 小的拿出這份日記 希望透過日記和照片 帶領大家也去全生園虛擬見學一回。
日本國立漢生病療養所~全生園見學經驗 


全生園的房屋大多已經翻修,看的出來都是近代的和洋式建築,後來有機會進到幾位歐寄桑的部屋,房間不是很大的和式建築,但是住一個人我覺得剛剛好裡面地板都是舖たたみ,後面有個人的小廚房還有一間廁所,沒有浴室 但是在園區裡有看見大浴場,猜測他們還是習慣公共浴場(我也很喜歡!) ,雖然部屋部大 但每間部屋外面都有相當大小的にわ(庭園) ,讓阿公阿媽們惹花捻草,整體生活空間寬敞,貼近大自然
其實建築物的部分站整個全生園並不大,從資料館旁邊小路走進去,兩旁是大概兩個人可以合抱的櫻花樹,高橋一開始就先問我們,知道為什麼這裡的櫻花樹特別粗
途中,我們可以任意穿越過一整片樹林,一個人影也沒有,感覺很像會有豆豆龍トトロ會出現的地方,結果


繼續走著我們來到了院區中的病院,高橋本人也沒有進去過,我們因為沒有事先預約,表明身分之後,是外科局長來帶我們「見學」(參觀) ,病院外表並不起眼 不如台灣醫院來的氣派,樓層也不高,我看是不會超過兩樓,病院入口雖不起眼 但是走道很寬敞,外科局長表示:這間病院因為是在全生園裡面,所以只照顧園區的住民,其實在日本已經不用患者來稱呼以治癒的漢生病人,他們都叫做「回歸者 かいうくしゃ 」就是從漢生院禁錮回歸社會的意思,(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說法,一方面尊重他們不是漢生患者的事實,一方面也可以教育大眾,消除對傳染病的疑慮)。

因為速度很快我常常來不及拍照,有些可惜,大體上我覺得這是一間很實際的醫院,雖然外觀並不起眼,但是對於回歸者或是患者是很友善的空間,儘管全生園裡的 花草已經多到不能再多,病院外圍還是種滿花草,有幾間大面落地窗設計以及某一些走道上方天窗設計,對陽光的進入,也是相當容易的,是一個友善而且實際的病院。離開病院,走著走著看見一群人在打野球,全生園裡有野球場,我大為驚喜想說他們的回歸者還可以打野球,走進才發現不是(我有時候還真佩服自己的想像空間),我們坐在場邊觀站一會兒,如果不是院民或是院方的人,外人也可以使用這空間嗎?那些是附近社區的人,高橋說,也就是只要有
我認為是很不錯的措施,可以促進外界的人對於她們的認識,把全生園當作是大家的綠色公共空間,市民運動休閒養生的好去處,這是一個不錯idea後面還有遇到一個神奇的阿伯,先要我幫忙找他叔叔的國小,要我去讀那一段歷史,他叔叔日本時代在台灣教原住民,是一位高雄州國小校長,然後開始電我古文, 還送給我們一人一本「菜根譚」加上他作的國畫手帕,那段插曲實在太神奇,到現在我還不敢相信。我也趁機參觀他的住所,偷偷幫他的有沖屁屁馬桶照相了,不過,這種廁所也是意料中的事拉!
雖然說全生園的房子很新很乾淨很整齊,外面有拿著Nikon相機的回歸者阿伯在拍花草,書子裡也有的阿伯飽讀經書,能詩能畫,整體設計幾經翻修之後現代化而新穎,院民也受到相當不錯的照顧,然而在院區裡走來走去,總覺得這裡似乎少了點什麼,和樂生院比起來少了很多歲月的記憶,歷史的遺韻
那時我覺得樂生院的才真有歷史的味道,難怪日人的紀念排上都寫「隱 匿的史跡」可見他們知道自己已經失去很多,由此可見樂生院有多珍貴。從全生園的廣佈綠地和政府對她們的照顧,讓人家覺得很窩心,讓人想到人權森林的名詞, 人權森林我在台灣聽過數百遍,但是在這裡所謂全生園人權森林的構想,我才真正看見,而且他們真的放一塊牌子寫著:將全生園變成人權森林的構想,如此看
尚儒 高雄 原文發表於06.06.28 第一次修改06.03.19
附錄
全生園簡介全生園是明治40年舊癩予防法制定後的基礎之下建立,明治42年為連合府県立療養所(公立療養所第一区府県立全生病院),收容関東1府6県:東京府・神奈 川県・千葉県・茨城県・埼玉県・群馬県・栃 木県以及新潟県・愛知県・静岡県・山梨県・長野県的廣大範圍之內患者,同年10 月18日開始收容病人,當時叫做全生病院,先在這個名稱已不用。即使當時以全生病院為名,應該是醫療救濟為對象,然而,實際上是目的性地將流浪在社會漢生 患者,從社會隔離收容的根絕的計畫。1941年移交厚生省後才改名為国立療養所多磨全生園。
原文当園は明治40年(1907年)に 制定された旧法である「癩予防法」に基づき、明治42年(1909年)9月28日関東1府6県:東京府・神奈川県・千葉県・茨城県・埼玉県・群馬県・栃 木県および新潟県・愛知県・静岡県・山梨県・長野県の広範囲をカバーする連合府県立療養所として、公立療養所第一区府県立全生病院として発足し、同年10 月18日からハンセン病患者の入所受入れが開始されました。創立当時はぜんせいびょういんと呼ばれていました。この呼び方が今でも残っています。 当時は病院とは名ばかりで医療の対象どころか社会救済の対象にもならず、浮浪徘徊をつづける「浮浪らい」と呼ばれていたハンセン病患者を社会から隔離収容し根絶を図るのが、主目的であったと聞いています。 昭和16年(1941年)当時の内務省の中にあった厚生省に移管され、これにともない名称も国立療養所多磨全生園となり、現在に至っております。
今天要跟大家談談漢生病和惱人的後遺症….
Leprosy: Modern History 近代漢生病史
1873 - Dr. Armaur Hansen of
挪威漢生博士發現痲瘋桿菌,頭一遭這個疾病與惡魔附身說法脫離
1950's - Doctors begin using Dapsone drug to treat leprosy.
醫師開始使用Dapsone(DDS)
1982 - Leprosy develops resistance to Dapson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commends Multi Drug Therapy of Dapsone, Rifampicin and Clofazimine.
痲瘋桿菌開始對DDS出現抗藥性,WHO建議使用三合一治療
漢生病雖然可怕,但是傳染力極低,即使WHO公佈的傳然途徑仍為不明,推測是由飛沫或接觸感染,但由歷史上可以知道,漢生病的流行常常發生在天災人禍的時候,營養不足或免疫力差環境之下,發生的機會較高。最近一個例子是2007年一月份時候,蘇丹的達富爾地區,因為長年內戰關係,難民營也發生漢生病的流行。所幸,Robert Cochrane醫師使用1908年即發現的DDS,在1946年第一個有效治療藥物DDS開始投入治療之後,clofazimine等藥物相繼問世,有人斷言,希望漢生病成為下一個被終結的歷史疾病
漢生病本身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往往是隨之而來的後遺症,針對症狀可做下列簡單的歸為四類:
1) 皮膚病變 :decreased sweating (DS) 無汗, anesthesia 知覺喪失, erythematous紅/ purple紫/hypopigmented白 lesions + ( macule斑疹/papule丘疹/plague斑塊), scaling脫屑, ulcer潰瘍
2) 神經病變 :thickened nerve(TN) 神經變粗大, neuralgia 神經痛
3) 四肢徵候: muscle atrophy(MA)肌肉萎縮, sensory neuropathy(SN) 感覺喪失, extriemities palsy(Foot drop FD/Wrist drop WD)肢體麻痺, limbs deformity (LD)肢體變形, secondary infection (SI)次發性感染
4) 五官徵候::cranial nerve palsy 腦神經麻痺, lagophthalmos兔眼(無法闔眼), Nose collapse(NC) 鼻褟陷uveitis眼球炎, cataract白內障, glaucoma青光眼

最常見的部位是手臂內側的尺神經,此外,鼻子、耳多和眉毛因為溫度較低而皮下容易寄居。總不能讓細菌在身體裡撒野,免疫大軍開過來是局部組織浩劫的開始。感覺和運動功能喪失加上莫名的神經痛說明了後遺症的原因,感覺喪失包含一般痛覺和溫覺,運動功能喪失來自於神經直接缺損而神經痛則是來自於局部神經因為免疫反應引起發炎物質所造成。因周邊神經病便感覺的喪失導致相當可怕的結果,不自覺的受傷,因為不會痛根本不知道傷口出現,導致已經感染,發炎潰爛,甚至嚴重到要截肢的比比皆是。運動功能喪失長期下來肌肉的萎縮也造成生活不便。因此,和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相似的手套襪子症候群也可以見到,Drop foot, drop wrist也不少見。
除了四肢問題外,因周邊神經病變眼睛閉不緊關不好(兔眼),造成接觸性角膜炎,進而角膜潰瘍,失明的也大有人在。難怪樂生院民不少阿伯終日帶著墨鏡。耳朵、鼻子的軟骨因為免疫反應分泌出來的一些發炎因子使的軟骨最終也遭破壞,很多院民的鼻子和耳朵不得不進行重建手術。
正因為傷口很難治療,所以漢生病有傷口的照護,也考驗一個療養所的能力,無論是硬體上的無障礙空間,與清楚標示危險區域,還有對於院友衛生教育,教導她們如何愛惜自己,避免受傷,例如,有洗屁屁功能的馬桶,可以避免院民因為不知道擦肛門的力道要多大摩擦造成傷口,又接近肛門容易二次感染,還有工作鞋的設計,避免足底受力不平均造成組織壓力性缺血壞死,等等不可輕忽。
雖然這只是些小小改變,但卻可以避免漢生病友後遺症發生,類似周邊神經病變患者照護,也是我們可以更深入探討的。
高醫 尚儒
本文出自於2005.04.05蘋果日報論壇
最近,在人權團體的邀約下,本組織實際走訪一趟署立樂生療養院,才理解到,在爭取「樂生院」保存的整個運動中,所挑戰的並非僅僅是「重大公共建設」擠壓「文化資產」的邏輯,更是檢驗各相關行政單位及民間團體是否真正具有關懷「弱勢正義」的高貴情操,而能不屈不撓地向「行政院」暨「台北市政府」提醒「人道考量在樂生」才是落實「人權立國」與「人權施政」的起始。
被捷運新莊機廠徵收土地而即將被迫拆遷的署立樂生療養院(以下簡稱樂生院),設立於日治時期,是全台「第一間」亦是日治時期唯一的痲瘋病院,更是全台至今唯一一
自主性空間優於醫院
走訪一趟樂生院,發現此處的照護品質相較於一般養護機構,優異之處在於:家庭式獨立住所、自行維護的寬廣庭院、與住宅相連的照護系統、各種就近提供的生活服務、
官員忽視人道與人權
從上述觀點來看,樂生院的保存,本質上是對人道關懷的延續,是人性化醫療服務產業的擴充。當初如果沒有捷運新莊線機廠強勢徵收,樂生院仍得面對伴隨院民人數減少
一,前言:疾病空間的知識/權力
近代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是因應近代社會、國家的發展而出現的,特別是伴隨傳染病流行的衝擊而產生。而傳染病控制的基本方式之一,是透過對於帶病菌者的發現(檢 疫)、隔離、治療,相對保護其他公眾者的健康。換言之,隔離空間的設置,成為必要的措施。由於公共衛生、防疫,牽涉公眾的健康事務,它賦予國家公權力介入 個人生活與空間,然而、公權力介入的合理與正當性如何?是否超越公權力介入的合理限度、而侵犯到個人基本人權?這是現代社會極為關切的問題。
癩病(俗稱麻瘋)是人類很古老的疾病之一,由於癩病發病的晚期,患者的外貌產生極大的改變,使其成為最為人恐懼、也最被污名化的疾病。就台灣近代防疫 史觀之,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引進公共衛生措施,近代式的傳染病控制也隨之出現。1930年創立的「樂生療養院」作為慢性傳染病、癩病防治的專門機構, 相較於日治前期殖民政府所處理的急性傳染病,樂生院隔離空間設計,有極為特殊之處,也成為反思疫病空間的重要議題。
台灣在去年(2003)SARS流行期間、發生疫病隔離的新衝擊之後,理解近代史上、癩病這種特殊的疫病隔離空間,也就有其嶄新的時代意義。本文在討 論「樂生院」疫病隔離的空間特徵以及其歷史變動,並思索這樣的疫病歷史空間、能提供台灣社會何種省思。
二,傳染病與空間的權力-殖民地疫病轉型與文明的象徵
傅科(M. 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的開場,談論著西方中古時期痲瘋病的故事。也就是西方中世紀時代,整個基督教世界、痲瘋病院曾經多達一萬九千間,至十 五世紀,多數痲瘋病院卻已空無一人。然而,就在痲瘋病從西方世界消失之際,乘載著精神錯亂者的「愚人船」隨之登場。傅科描述從「隔離痲瘋」轉向「放逐精神 病患」的歷史現象,主要為指出:痲瘋病雖然消退了,但西方人附加在痲瘋病的價值觀與意象,即排斥或恐懼痲瘋,附加其可怕的負面形象,仍然深固的持續著;而 且這種社會心理更轉向排斥精神病患、貧苦流民、罪犯等。傅科實深刻的指出:人類排斥弱勢以及邊緣者的心理結構,有著驚人的固執與延續性。
誠如傅科揭發的、人類排斥疾病有其延續性的心理結構,樂生院之作為痲瘋病隔離的機構,存在值得深究的社會心理。同時,這種對於傳染病的恐懼與排斥的心理, 某種程度也反映在隔離空間的設計,樂生院之成為痲瘋病終生隔離的空間,也不外反映人類對於痲瘋莫名的恐懼。
1895年日本治台之際、已仿效歐洲國家,確立以西洋醫學作為國家醫學的主體,特別是採取德國醫學體制,並且在防治急性傳染病的過程,建立公共衛生制 度。日人治台之初,又遭遇風土疫病流行的衝擊,為減少日人生命與健康的耗損,以及鞏固殖民統治,不僅加強近代衛生設施,也重視傳染病防治。而日文稱為「避 病院」的傳染病隔離所,在1896年鼠疫防治之時、首度設置。
近代國家對於傳染病的控制,以影響迅速而廣泛的急性傳染病如鼠疫、霍亂等為優先。日本治台之後,對於傳染病的防治、也不例外。1920年代以後,總督 府著手如結核病、癩病等慢性傳染病的防治,樂生療養院在1930年正式設立,也是屬於殖民地公共衛生的發展脈絡。
不過,樂生療養院的出現,也非僅是從急性、到慢性傳染病控制的必然結果。相關的背景因素包括:在台灣的日本醫學者提出,在台日人處於被台人癩病感染的 高度威脅,以此警示殖民政府;以及教會醫院、特別戴仁壽醫師對癩病診療、照顧的積極作為。加上,日本「癩病防治之父」光田健輔建言:外國傳教士對於癩病醫 療有影響人心的作用,希望台灣總督府能重視此事,並且取代之。
總之,1930年「樂生療養院」之設置,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除了殖民地公共衛生、防疫重點轉型之外,主是日人在台定居人口增加,恐懼殖民地慢性傳染病 的威脅;以及殖民政府深恐教會醫院對癩患診療的影響太大,而欲取而代之,以展示推展文明醫療的作為。即在這些殖民地政治與社會心理的影響之下,終於出現這 座大規模的隔離醫院。
三,樂生院的空間設計與終生隔離的概念-疾病認知的侷限與過度恐懼
1927年,台灣總督府以三年為期,開始在新莊興建「樂生療養院」,也正式開啟台灣的癩病防治。日本早在1907年公布有關癩病預防的法規,確立癩病 為傳染病而有必要隔離,在全國各地設立五個癩療養所,初步以收留流浪癩患者為主。因此,台灣不僅延用日本相同法規,而且對於療養所的建築設計,也參考日本 熊本九州療養所(現今稱「惠楓園」)與東京府的全生病院(現今稱「全生園」)。
當時日本癩療養所的特點,主要是依據傳染病的細菌學概念,區別為「有菌」、「無菌」兩大部分,以及建設生活機能完整的設施,也是近代日本對癩病採取傳 染病隔離的明確表現。1930年完工的「樂生院」,也具有這些特點。該院於同年12月開辦,正式收容患者,最初僅有日、台籍五人入院。至第二年年底 (1931)收容人數達百餘人,已達到其預定收容的100人。如果以當時官方調查的全臺癩患人數,歷次癩患者調查,皆在六百人以上,相較於樂生院規劃百人 的收容量,顯示官方初步措施以收留流浪癩患為主。
| 就這初期療養所的建築空間,如圖一:從正門進入院區,除正門左側有守衛室之後,全院主體建築呈王字形,王字形第一進「行政廳舍」,開放對外的;從王字形 「中央走道」進入第二進之後,右側是「治療室」,左側是藥局、醫藥室、試驗室;其中,較為特別是從中央通道有一向左叉出的通道,直接通向「藥局」。這樣設 計的關鍵在第二進「中央」的「更衣室」,也就是管制從第二進到第三進的「有病菌區」必須「消毒」、「更衣」,因此為進入「藥局」又避免「更衣」的不便與費 時,即是走左側叉出的走道。接著,從中央穿堂連通第三進,即為重病室,左側可通達禮拜堂、預診室,右側通達「停屍間」。 |
這樣的空間分配,清楚顯示「有菌」、「無菌」的空間區隔,即以第二進「更衣室」為管制點,在此之前的「行政廳舍」是無菌區域。此外,位於遠離院區主體建築的左側,即看護婦(護士)宿舍和官舍也是「無菌區」。
除此之外,凡患者活動的空間都是「有菌區」,包括從第二進中央「更衣室」為起點,第二進左、右兩側醫療空間,連接第三進的中央通道,以及第三進左右兩 側。同時,輕症者住宅位於「重病室」左上方以及左外側,共計四間「患者住宅」,藉山坡較高的地勢,與「重病室」作區隔;另外,在「重病室」右上方、是提供 患者日常生活需要的「浴場」、「炊事場」(廚房)、「機關室」(蒸氣消毒室)。
而這些患者生活的空間又有監視、禁制的設施,嚴格的管制。如院區外圍周邊的「鐵絲網」,以及設置兩個「消毒槽」,一個如前述的、在「王字形」建築中央 的「更衣室」,另一在左側、「預診室」前面,設「守衛」監視之。而就在左側「守衛室」之外,特別開設一「患者通用門」,並另設一條左側小徑為「患者道 路」,直接通到縱貫道路,顯示患者進、出院區都由此特定路線。此外,處理違紀患者的「監禁室」,設在「王字形」建築斜右外側、一單獨空間。
上述的空間設計,無論是「有菌」、「無菌」的分類與空間區隔,或採取戒備森嚴的空間管制,顯示對於癩病戒慎恐懼的心理。然而,從近代醫學、細菌學的角 度觀之,當時日本醫學以及公共衛生學界對癩病持如此戒慎的心理,並非合理之事。
近代所謂癩病(leprosy),是1873年挪威醫師韓生(Dr. G. A. Hansen)因發現癩病原菌(bacullius)證實為傳染病者,並認為強制隔離是最佳的防治措施。然而,Hanson發現癩病原菌之後,在動物試驗 及純培養試驗又呈陰性反應,並不符合近代科學醫學的細菌學原理。其中所顯示的意義,乃是當時部分醫學者所主張的、也是爾後醫學研究證實的,癩病雖為慢性傳 染病、但也是最不容易傳染的一種。因此,對於癩病施行如此嚴密的分類、隔離,不僅是醫學界對癩病認知有限所致,也是因傳統上對於癩病的附加想像,而造成過 度戒備和恐懼的結果。
此外,樂生院的空間狀況有些在圖一並無法顯現出來的,是以照片影像刊載出來的。這些影像不僅呈現癩病患者的日常生活空間,從學習、勞動、娛樂以及宗教 等各方面,說明患者以院為「家」的良好生活;以及新式而進步的醫療設施,宏偉美麗的廳舍建築。整體上,營造出樂生院頗為吸引人的近代醫療,以及文明進步的 生活情境。這些文明醫療與生活情境,實際存在或經由某種想像而傳達,似乎有宣傳效用。
基本上,日治時期台灣癩病防治是日本帝國公共衛生的一環,除特殊的殖民因素之外,主要受日本本國公共衛生政策的影響。當1930年代初日本癩防治法修正, 而殖民政策也強調「內地延長主義」,台灣的癩防治法終究也隨之修改。其中,有關公共衛生的連動發展,是加強癩病的強制隔離措施;而反映在樂生院的空間,乃 是院區空間的變動與擴充。這也顯示國家公權力對於人民生活介入的增強。
從樂生院歷年院區地圖觀之,1934年(昭和9年)之後、院區空間開始有比較大的變動。背景因素是1934年台灣總督府公布「癩預防法」,延用日本在 1931年制定的癩防治法規,重視強制隔離措施。因此,樂生院收容患者人數快速增加,院區也隨之擴充。1935年,樂生院收容定額增至227人,1938 年收容定額為587人,然至年底實際收容已增至628人;至1939年收容定額達最高額之700人,至日本治台結束為止。
1931年日本「癩預防法」修正,主要是著重充實防癩經費、從業管制、加強檢疫與報告病例、管控私人相關機構等,這些皆有助於增加國立療養所收容癩患 者人數。而在殖民地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也就是強化警察取締癩患者的權力,及因充實經費而能取代、或減少教會療養所的影響。
同時,台灣總督府為落實新法執行的效力,成立社會事業組織,籌募相關經費與取締方案,樂生院空間因此大幅改變。1933年6月總督府在尚未修正癩預防 法之前,先成立「台灣癩預防協會」,以協助防癩宣導以及促進相關預防設施為目的。該會成立之後,首要措施是推動模仿日本設置小型療養所「十坪住宅運動」, 在減輕官方經費負擔之下,有效擴充樂生院療養空間。
至於落實警察取締癩患一事,除總督府警察部門調查癩患的次數增加之外,台灣癩預防協會也推動,由樂生院醫療人員組織的調查小組,選取各地特定村落、一 般是癩患者分布較多的地區,如澎湖廳、台北州、高雄州、台南州等執行細密的調查,一方面也在檢驗警察部門癩調查的可靠程度,並因此證實其有所落差,而新發 現不少病歷例。
| 據此,樂生院的空間變動,可以1937年、以及1939年兩張地圖分析之。就患者收容觀之,1937年年底患者數是433人;而1940年年底是635 人,幾乎達院區最高容量。首先,就圖二、圖三:1937年樂生院地圖,整個院區的擴大最顯著的,就是經由十坪住宅運動新建的,包括在圖的右上方的「光山 舍」、「漁翁舍」、「雙愛舍」,以及左上方的「婦慈舍」、「喜一舍」、「東高雄寮」,共計六棟。此外,在原來「患者住宅」正上方以及左上方、增建三合院式 的「患者住宅」,共計九棟。院方建築這種三合院式,顯示考量台人居住習慣、或可說是長期療養生活的做法。 |
從1937年的地圖,還可見幾項新增設施,也是「台灣癩預防協會」推動的。包括:正門入口的左側通道上設置「保育所」和「面會人免費住宿所」,「保育 所」也稱「新生寮」,是提供收容未感染兒童之用;以及圖右側的「特殊患者住宅」,也稱為「昭和寮」,提供經濟富裕的患者獨居之用。另新出現的專屬空間有: 「賣店」、「木工部」、「恩賜紀念運動場」。以及在圖頂端的、日本國家神道信仰「神社」,而從院區正中間出現一條「中央路」、直通「神社」,也顯示如此政 治空間的重要性。此外,另有一重要衛生設施是左上角的飲水設施。 |
其次,就圖四、圖五:1940年樂生院地圖,由於此時樂生院已達最高收容量,成為戰後樂生院空間的基礎。此時空間顯著的變動在於:原來的護士與職員宿舍 從偏離院區的左上方,轉移到最右下方,而且宿舍、佔地空間也大為增加;而讓出來的宿舍空間轉為患者住宅,總計新增十四棟住宅。以及左下方有一大片患者耕作 的田地。 整體觀之,在樂生院隔離空間的擴張過程,除為因應患者人數增加而擴建患者住宅之外,充實患者療養生活的空間也隨之增加。這些設施不乏因應台人生活習慣者,當然也具有強化對日本帝國忠誠的政 | |
| 治設施。此外,從當時樂生院大風子油治療成果報告,顯示樂生院也是兼重實驗治療研究的。 | |
無論如何,1934年以至日治結束,樂生院作為癩病強制隔離的機構,透過衛生警察或醫療人員普遍調查、檢疫、監禁癩患的過程,終究造成社會恐懼氣氛,加 深對痲瘋的歧見。當時日本帝國仿效北歐(挪威)的做法,對結婚患者施行節育處理,也是假「公共衛生」之名,即藉著維護公眾社會健康的名義,枉顧癩患人權的 做法。 當時日本對於癩病採取極端的公衛措施,一方面是近代醫學在癩病醫療的侷限,另一方面日本將根絕癩病、視為作為文明國家的必要條件,因此衛生官員重視宣傳癩病毒的危險性,以及對癩患施行絕對隔離、禁絕生育。當時、殖民地台灣防癩措施既以日本本國為依據,似乎 | |
| 較難違抗日本醫學界的主流看法。也因此,樂生院終究成為強制隔離以及終生監禁的機構。 | |
五,反映戰後政治變局與社會偏見的空間:被社會隔離的新院區
1945年日本殖民時代結束,台灣歷經政權轉移。國際癩病防治也轉向新的里程碑。1940年代中期抗癩特效藥、磺化藥物普羅敏(Promin)及戴普松 Dapsone(DDS)的使用,有效抑制癩桿菌。以及1960年研發能完全治癒癩病的Rifampicin與Clofazimine。因此,國際間倡議 新的癩病防治措施,鼓勵採取尊重人權的開放處理,及門診治療方式。
在戰後癩病醫療的新時代,台灣對於癩病處理也轉向新措施,即1954年起、於全台各地陸續設立皮膚科門診、所,非開放性癩患者轉由各地門診管理。然而,新莊樂生院癩患的處遇仍面臨許多難題。
首先,在戰前被強制隔離於樂生院的患者,雖然試圖返回家鄉,然不少人終究因「痲瘋」的污名,社會關係的疏離,而被迫再度返回樂生院。換言之,儘管抗癩的藥 物進步了,但社會大眾對於痲瘋的歧見並未消除,他們僅能退回到原來與社會隔絕的世界。繼之,戰後初期另一波新移民進入台灣,當時撤退來台的軍民之中,發現 不少癩病患者,樂生院仍是主要收容機構,收容人數最多達一千餘人。就此,樂生院成為新、舊癩患者共同的家園。
基於戰後台灣新的政治、社會脈絡,樂生院空間又有變動。首先,戰後防癩措施轉變最重要的象徵,是1954年樂生院方撤除院區四周鐵絲網。繼之,因應從 軍方送來的癩患者,開始增建新病棟,是就原有院區病棟的外圍加以增建。即在1950年代軍醫署、退輔會先後撥款新建軍患病舍,包括:經生、惠生、靜生等。 以及1966年又完成啟用新建盲人病房。1975年,增建新生甲、乙、丙等病舍。這些軍患、榮患病舍大抵是分布在院區左、右兩側外圍,或偏左上角的邊區, 反映作為院區新族群的空間特徵。
在戰後樂生院的新建築之中,最有特色與意義者莫過於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三種宗教建築,這是緣於三種宗教對於院區病友,發揮無比愛心與長期照護。其 中,基督教孫理蓮牧師娘的芥菜種會是最早進入救助病友者,也首先在院區設置教堂,聖望教會禮拜堂(1952年完工),發揮長期救助病友的最大力量。
在聖望教會禮拜堂建成之後,院內佛教徒大為所動,決定動手新建佛堂,由院友金義楨統籌其事,選定當時院區低漥陰濕的空地填土,病友們一磚一瓦將搭蓋佛 堂「棲蓮精舍」,於1954年5月落成。繼之,輔仁大學古神父籌備創建天主教堂,於1971年4月完工。另一由病友同心協力完成的建築、是消費合作社與理 髮廳,於1960年完工,樂生院提供建材、病友自行建造,牆上木板刻字與房頂「樂生」二字皆是病友製作。
戰後,樂生院雖然逐漸脫離作為公共衛生上、癩病隔離療養的定位,然而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它依然被隔離於台灣主體社會之外,即在此意義上、樂生院仍是被社會 隔離的院區。然而,就在這被社會隔離的空間之內,樂生院病友在宗教團體的支持與精神安慰之下,發揮殘而不廢的精神、自力更生,默默的貢獻台灣社會,使這個 院區迴盪著許多他們打造家園、貢獻社會的故事。
六,結語:樂生院與日本人權森林的構想
關於人類疾病史,不少學者指出:疾病雖是一種生物現象,然而人類對於疾病的理解、卻無法自外於其社會文化脈絡,疾病既是生物現象、也是社會現象。生物性的 疾病固然可怕,但人類因社會文化的偏執和恐慌,所造成的疾病迫害,可能比病菌更為嚴重。
人類最古老的疾病之一的癩病,就是這樣受到人類各種偏執所扭曲的一種疾病,無論傳統社會視痲瘋為一種「天刑病」或遺傳病,並如傅科所言、採取絕對隔離 的方式、將其排除於社會之外;或者當近代國家的公共衛生發展之後,以維護公眾健康的的正當性,合理化對癩病患者強制隔離措施;或甚至在戰後,抗癩藥物進 展、患者已呈無菌狀態,但社會歧見仍附加其上,癩患者仍處於社會邊緣。樂生療養院、這樣深刻的銘刻著對癩病偏執的歷史空間,它實提供給台灣社會許多重要的 省思。
1.什麼是漢生病?(俗稱痲瘋病)
漢生病俗稱痲瘋病,是一種侵犯皮膚及週邊神經之疾病,由癩桿菌所引起,故又稱癩病;1873年,挪威漢生醫師發現致病機轉,故學名稱為漢生病。
癩桿菌是一種連在實驗室中,都不易培養的菌種,傳染力極弱,百分之九十的人,有癩桿菌自然免疫力。人類是漢生病的主要傳染源,上呼吸道是主要入侵途徑,潛伏期約三至五年,最長可達四十年。漢生病好發於公共衛生條件不佳的地區,以台灣目前的公衛條件,漢生病幾乎不具傳染力,且當前已有藥物可以治療。
2.為什麼過去會實施強制隔離政策?
20世紀初,歐美等進步國家因公衛條件改善,導致漢生病幾乎絕跡。然而,當時一心想師法德國的日本軍國政府,面對日本國內(含海外殖民地)為數眾多的漢生 病患時,將漢生病患視為「國恥」,並於1907年著手制訂「癩預防法」,計畫將漢生病患強制隔離於社會之外,營造漢生病「絕跡」的假象。
3.強制隔離政策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日本政府在推動強制隔離政策時,妄自誇大漢生病傳染力,強力對社會宣傳、教育痲瘋病的恐怖,並動用軍警力量及民間通報系統,將病患強制「逮捕」入院。這種 在家人、朋友、街坊鄰居面前被公開逮捕、歧視的經驗,以及該政策所造成根深蒂固的污名,使得漢生病患在強制隔離措施解除之後,仍然無法回歸社會,造成「有 家歸不得」的悲劇。
4.若政府要立法保障漢生病友權利,我們認為應包含哪些面向及原則?
2005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時代遭到強制隔離的台灣漢生病友,在東京地方法院獲判勝訴,比照日本的病友獲得賠償。因此,陳水扁總統表示要補償救濟在 國民政府時期被強制隔離的漢生病友。如果台灣政府誠心認知到過去強制隔離政策是國家對於漢生病患的人權侵害,則應該參照日本漢生病補償法的立法精神,平反 病友受到的歧視與污名,恢復他們的尊嚴,促進他們生活與照顧品質的提升,幫助他們安享天年。因此,立法應比照日本政府的作法,至少包含一、「恢復名譽」、 二、「適當的精神與物質方面的賠償」、三、「提供入院病友尊重其意願的照顧與福祉」、四、「終生在園保障」(即便是最後一名院民,也保障他終生在療養院內 的居住權與健康權 )等內容。
5.為何捷運新莊機廠選址在樂生院是一個錯誤政策?
一、開挖大量土方浪費社會成本:此機廠有五分之三為山坡地需剷為平地,要花費近三十億元進行大量土方開挖與改良地質。
二、破壞當地生態環境與景觀:山坡開挖創造十層樓高的檔土牆,對於當地生態環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三、機廠設在新莊斷層帶,有安全性上的疑慮。
四、對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樂生院是東亞史上重要的文化資產,此工程將整片山坡剷平,珍貴史蹟將化為煙塵。
五、對於院民醫療照顧品質的危害:工程嚴重影響生活品質與醫療照護,同時剷平院民的家園與生活點滴,對年老殘疾者來說,是生理與心理上最大的酷刑。
六、決策過程的不民主:最根本的問題是,在捷運選址於此的過程中,未曾徵詢當地住民「樂生院民」的意見,是非常違反基本人權的作法。
6.為什麼迴龍醫院是一個錯誤的安置計劃?
迴龍醫院就如同一般醫院,規劃設計是以短期住院病患為考量,因此沒有足夠活動空間的高層電梯建築,對行動不便的院民而言,處處是障礙。此外,在管理上,院 方最初採取禁止攜帶個人物品和家具、不能自己煮東西吃、代步車需集中停放在停車場等病院式管理、更有限制院民不准到前棟影響醫院營運等歧視政策。
然而,漢生病友需要的不是醫院,而是生活機能完善,以及自然安適的環境:平房式的建築、大樹的綠蔭、花木的綠地、走動散步的空間。因此,最佳方案應是在舊院區進行整修,提供全面而完備醫療和看護。
(在社會運動的壓力下,衛生署已將「迴龍醫院」的招牌卸下,改名為「樂生療養院」及其「迴龍門診部」,然而,換湯不換藥,醫院終究是醫院。此外,雖然安置院民的後棟建築也做了許多改善,然受限於主體建築已經完工,只能針對隔間、家具與管理方式等進行改變。)
7.他國如何對待漢生病友?
經過漢生病友、律師與社會各界多年努力,日本政府已於2001年認錯道歉,並立法補償,推動漢生病友人權保障與名譽恢復相關政策。
在生活照顧方面,以日本長島愛生園為例:愛生園保有舊院舍與長島自然景觀供社會教育用,院民居住在經整體規劃的人性化平房房舍,園區整潔、有遮蔽風雨的廊道,又考量許多病友眼睛失明,交叉路口更設有警告播音、提供盲人收聽的廣播系統等。醫療資源充足,醫療人員和病患比例將近2比1,每位院民皆可獲得完善的居家照護。
8.已有部份的院民搬離舊院區,樂生院為什麼還需要被留下?
多次「捍衛家園」的抗爭下,「迴龍醫院」後棟建物(今已更名為「樂生療養院」)內裝一修再修,今日已有許多院民在自願、半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況下遷入。我們 尊重自主搬遷院民的意願,但仍認為「迴龍醫院」的決策過程不符合公平正義,其結果也問題重重,是個錯誤的政策。院民選擇居住在舊院區的權利不可被剝奪,因此我們反對任何挾醫療資源脅迫年老殘疾的院民搬遷的手段,只要還有一人想要住在舊院區,就不該拆除樂生院。
除此之外,樂生院銘刻了漢生病友隔離歲月的點點滴滴,是醫療史、人權史與東亞史上珍貴的史蹟,站在文化資產保存的立場,院區應該被完整保存下來,供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後的子孫反省這段歷史。
9.樂生院只有七十多年的歷史,真的有古蹟保存的價值嗎?
文化資產的價值不全然由年代的久遠來斷定,更重要的是它的歷史意義。樂生院具體展現了人類對於被污名疾病的「隔離」與「滅絕」思維,以及日本殖民政府的 「民族淨化」政策等重要的歷史意涵,也表現了漢生病友強韌的生命意志—用殘缺的手腳把集中營般的隔離空間打造為美麗可居的「家園」,對於當代有豐富的社會 省思與人權教育的意義。
樂生院就其公衛史、殖民史與人權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文化價值切合多項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於文化景觀的評判標準,已獲得國內外相關的專家學者的認可,並先後被桃園縣與文建會列為暫訂古蹟予以保護,是屬於世界級文化資產。
10.拆遷重組或部份保存不行嗎?為什麼堅持一定要全區原地保存?
現今的文化資產保存的國際潮流,不單是保存建築物,還強調保存「人」與環境的關係,也就是所謂「『活』的保存」與「活古蹟」。樂生院是院民們用曲折的生命 營造而成的活古蹟,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紀錄著他們隔離歲月的苦與和命運搏鬥的光輝。部分保存或是拆遷重組的保留方式,將完全破壞樂生院蘊藏的生活紋理與生命記憶,如此保存下來的房子是「死的」、沒有意義的。
此外,樂生院保存重要的目的是提醒社會,曾經有人受到錯誤政策迫害一生。樂生院若採破壞式的拆遷重組保留,強迫院民遷走,是二度的人權迫害,這樣的人權反省史蹟,只會成為水泥叢林上,最荒謬的空中樓閣。
11. 是否樂生院不拆,捷運新莊線就無法通車?
樂生院民的居住權益與捷運新莊線通車的問題,為社會大眾所關切,我們同樣關心二者的共存共生。台大城鄉所劉可強教授曾於民國93年12月,提出「捷運樂生 共構方案」,不但原地全區保存樂生院,捷運也能通車,達成古蹟、捷運、院民與迴龍社區四贏局面,此方案也經捷運局評估為「技術可行」。然而,當時卻因內閣 總辭,在未召開任何會議的情況下,負責本案的政務委員以一紙公文草草判下樂生死刑,共構方案自此遭到擱置。
樂生不拆,不必然是阻礙捷運的絆腳石,只是政府壟斷了黑箱中的「技術資源」與「法律霸權」,然後將捷運延後通車的責任轉嫁給樂生院民。如果政府不願意停止 拖延錯誤決策的平反,將黑箱透明化,卻一再敷衍與推卸政治責任,則它將不只是毀了樂生院,也達不到捷運通車,損害了樂生院民與所有市民的權益。
關於40%方案與90%方案對於建築群的影響,歡迎參考圖示:



http://sdkfz251.blogspot.com/2007/03/90.html 轉載自廢業青年日記 blog
12. 樂生院從十多年前就規劃為機廠用地,現已完工一半,為什麼這麼晚才提出保存的訴求,難道不會為時已晚嗎?
其實十多年來,反對機廠設址樂生的訴求,就不停的被各單位提出。
早在水土保持評估進行時,就有多位學者提出挖方超量的問題。此外,省衛生處也在民國83年表示工程將嚴重影響病友生活品質,且施工過程將波及肢體殘障的病友的生命安全,因此這個規劃案「絕不可行」。同年,樂生院民也開始抗爭,表達誓死捍衛家園的心聲。
而在機廠開工前,樂生院前院長與文史團體就曾要求進行古蹟審查。前往會勘的古蹟學者全數強烈要求保存樂生院,呼籲捷運機廠另覓地點或變更設計。然而當時捷 運局卻恐嚇說:「只要部分原地保存,增加的工程費用將在百億以上」、「除非(機廠)不做,否則原地保存不可能」。當時的台北縣政府也中斷古蹟審查程序,並 決議全區拆除樂生院。
直到93年底在劉可強教授提出共構方案,以及94年初桃園縣文化局與文建會暫訂古蹟等一連串的壓力下,才讓捷運局開始改口承認變更設計原地保存樂生院的可能性。
捷運局前後矛盾不一,用偏離事實的工期與經費評估,恫嚇文化單位和社會大眾的做法,顯示出「為時已晚」其實是工程本位心態下的慣用拖詞。不論地方或中央, 工程、文化及衛生等單位敷衍塞責和傲慢欺瞞的態度,才是爭議越來越難收拾的元兇。我們期待政府單位不要再以類似「工程已進行,來不及了」的謊言繼續犧牲文 化資產和院民權益。
13.樂生院有保存價值,院民的人權也很重要,那麼其他民眾的權益難道不重要嗎?
捷運局長期使用「國家重大建設」、「維護公共利益」、「一百萬人的通車權益」等字眼,將樂生院塑造成「一小群人阻礙捷運」的問題,導致樂生院的保存,被化約成天秤稱重的簡單思維,好像「利益」傾斜的一方才屬於正義、符合眾人期待。這樣的想法並不正確。
首先,如果我們認識到樂生院是全台灣與後代子子孫孫的重要資產,也是世界上每個曾經實施漢生病隔離的國家所共有的財產,同樣也是一種「公共利益」,天秤上 的樂生院就會有不一樣的重量。若政府願意改以積極的作為,從共生的可能性著手解套、促成人權森林與樂生文化資產景觀的誕生,那麼當地居民不但因此多了一塊 休閒綠地,迴龍地區更能因為樂生院的存在而發展出以人權與歷史文化景觀為意象的新地方精神。
再者,在台灣這樣地窄人稠的地方,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有可能會在某一天受到公共工程的衝擊(土地被徵收、生活環境被工程破壞等),如果我們今天同意政府對 待樂生院民的粗暴方式,明天同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在民主化程度高的國家,如日本,社會往往願意花上相當長的時間,等待公共工程遇到的民眾權益 問題有比較好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要求政府負起責任,用保障弱勢人權、尊重文化與保護生態的態度處理樂生院的爭議,也是為了保障我們自己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