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簡介戰後日本及韓國的癩病防治歷程
他山之石:簡介戰後日本及韓國的癩病防治歷程
文/陳歆怡
文/陳歆怡
本文經作者同意 全文轉載自樂生院人間寫實
http://blog.roodo.com/losheng/archives/1445745.html
前言
戰前的日本作為後進的殖民主義國家,在二十世紀前葉以超越西方人的嚴厲作風處理被視為「國恥」的癩病,受日本殖民的韓國、台灣則先後成為日本處理癩病問題的實驗室,癩病不僅被要求限期撲滅,更被污名化甚至被罪犯化,這段幽暗歷史終於在去年(2005年)日本政府對兩地療養所戰前隔離病患給予賠償之行動中,得到關切與平反。
戰後,台、日、韓在癩病防治工作上卻走出各自不同的路徑。在制度上,台、韓在戰後不約而同轉向門診為主、住院為輔的防治策略,且同受教會醫療影響甚深,日本則始終以國立療養所收容大部分患者;
在社經條件方面,戰後的台、日、韓比起亞洲其他癩病流行疫區,在醫療、社會福利、教育文化、交通及通訊等各方面有更多資源可以投注在防治及照顧工作上,而日本最早取得流行率的控制,其次是台灣、韓國。這些表面的異同背後,究竟有什麼內在的關連?本文僅在拋磚引玉,相信參照日、韓戰後的癩病防治歷程與釐清其社會環境背景,可讓吾人更覺察到自身經驗的特殊性及侷限性。
日本經驗
在日本,以強制隔離為旨的「癩預防法」自1931年成立後,一直維持到1996年才廢除,日本學者檢討隔離法的僵固性來自於:癩病議題始終侷在特定、封閉的醫學圈內,癩病專家經常身兼政策諮詢委員及療養院院長,傾向採取/採信隔離的有效性;行政官僚比較在意既定預算能否確保,而非制度的改革(Hajime Sato & Minoru Narita,2003)。不過,療養所在實際執行上乃優先隔離貧窮患者,有錢人允許其在家隔離治療,並設監視機關來監督。60年代以後,療養所的管理逐漸鬆綁,允許患者進出,但是整個社會對癩病患者的歧視還是很嚴重。1980年時,16個療養所共收容8700餘人,居家治療患者僅有2700餘人。
1950年以前,日本每年新發現罹病人數在600人以上,1963年以後降低到每年新發現病人在200人以下,1968年起降到100人以下。日本醫界相信,癩病傳染率快速下降的主因是實施隔離收容,對醫療機關管理上也比較方便,但長期投入高傳染率的沖繩縣防癩工作的醫師犀川一夫卻提出異議,認為唯有居家治療才能使病人由消極逃避轉為積極治療,患者無須離開職業或家庭,並能兼顧預防及消除偏見的雙重目標。
無論如何,特殊的制度因素使得日本患者多數住在國立療養院中。這樣的群居經驗使得患者及其家屬很早就形成集體組織,在戰後民主化浪潮的激勵下,政治性抗爭早自1950年代起開展,早期訴求包括取消強制勞動、加強醫護設施及引進新藥。患者面對1970年代之後提到議程上的廢除癩病預防法主張一度遲疑不決,患者主要是擔心廢法後療養所的經費會減少,甚至會被強制出院,而政府方面也未對回歸社會有明確規劃。1993年,高松宮韓森病資料館落成,患者積極參與館藏蒐集及解說,引發社會廣大迴響,廢法及補償運動隨之積極展開。1996年「癩預防法」正式由國會廢除,並相應提出後續安養保障措施。1998年癩病患者對政府提出國家賠償要求,在2001年勝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放棄上訴並公開道歉。
當前,日本社會普遍承認這群癩病患者為「犧牲者」。1977年時,療養所內收容的患者超過50歲人數已佔70%,這些老年人除了要求充足的醫療及終生保障作為過去犧牲的彌補,並期待社會人士能夠尊重其獨立性、給予平等對待,同時欣賞其經驗及知識仍有貢獻社會的價值。又由於日本社會經歷快速高齡化,老人醫學與復健問題在日本受到高度重視,連帶充實了癩病療養所的設施與機能。總之, 日本癩病患者晚年享有的福祉及保障,是在社會經濟條件相對富足的情形下,透過患者組織與人權團體漫長的運動過程爭取而來。
韓國經驗
在韓國,殖民時期除了1913年殖民政府設立的小鹿島慈惠病院外,還有美國教會醫師R. M. Wilson於1909年設立的麗水復生病院。戰爭期間,許多收容患者流落街頭。1945至1957年間還發生過多次屠殺癩病患者的事件。這段期間並有私人及教會醫師設立門診,組織勞動聚落,扶助患者生活及醫療照顧。1962年,大韓癩協會在政府提倡下成立,與教會等民間組織合作,在全國設立10個分支機構、20多個巡迴醫療隊,全國202個保健所並有癩病個案工作員從事追蹤管理,另外,政府自60年代起有計畫地將流離失所的患者以及具有勞動能力的患者集中在100個定著村(settlement vallige),扶助患者從事農牧生產。
自上述防治體系建立後,韓國政府登記管理的病例逐年增加,1975年之前均超過3萬人,1978年統計出居家病患13389人(佔47.6%)、住院病患4954人(佔17.5%),居住於全國94個定著村的患者則有9815人(佔34.9%),連帶住於定著村的家屬在2萬人以上,當年另估計仍有2萬多名隱匿患者。至1982年止,全國每年仍發現新病例400人,全國估計有5萬名患者。
韓國政府的防癩政策採取門診與住院並行的治療模式,由於患病人數居高不下,社會復歸問題受到高度關注,對策包括:按經濟狀況補助醫療費用,貧窮者另給予家庭救濟;患者痊癒即出院,或安頓至定著村;幫助住院病人生活所需及子女獎學金,代為尋找工作或貸款;訂定法律條文保障患者生活及工作;職訓中心接受癩病患者包括殘障人士,提供一年的職業訓練。另外,設置護理之家安置年老病患。日殖時期成立的小鹿島療養所是唯一的國立癩病療養所,現為一國家公園,仍有特定癩病患者--高齡患者或殘疾狀況嚴重者--居住其間。目前,韓國還剩下80幾個定著村,人口多已老化,而定著村落後的環境及第二代子女的問題逐漸成為新的問題。
對照日、韓經驗,可以給台灣什麼啟示?
韓國及日本的經驗都顯示,癩病患者的疾病身份仍是一個顯著的社會分類並持續受到制度性的區隔。兩個國家各有其特色:韓國的社經條件與台灣接近,但是,台灣的登記案例如以1977年的最高紀錄4942人為計,則韓國案例數是台灣的6倍,韓國長年以來癩病患者人數居高不下,如何提升生產力於是成為急迫的問題,因此而有政府輔助設立的定著村。70年代時,全國三分之一的雞蛋曾經產自定著村,可見其經濟自立程度。韓國的經驗對台灣的啟示在於,政府在推動門診治療策略時,必須有其他配套措施才能達到扶助患者復歸社會的目的,但是韓國經驗或也提供這樣一個質問:在癩病這種弱勢疾病的議題上,行政官僚之所以會展開醫療-勞動-社工跨部門的分工合作,而非掃到一旁、藏到角落,道理之一在於該弱勢族群的人口數是否龐大到足以「威脅」主流社會的安全,以致社會不得不正視它的存在--包括正視其對社會還有生產力?
日本對於癩病的大規模、長時期的隔離則反應了社會深層的恐懼。日本社會有所謂「賤民階級」觀念,過去癩病即屬於賤民範疇,並且是日本帝國主義時期「民族淨化論」高張下的犧牲者,因此,日本戰後彷彿集體救贖般願意投注大量資源在這些人口的照料上,即便防治目標已經達成,仍持續從事醫學研究並將成果回饋國際社會。另一方面,日本患者運動經驗除了反映相關醫療人權及公害賠償運動所積蓄的社會能量已達到一定高度,也意味癩病患者個人的受苦經驗被昇華至道德象徵的層面,全面性地平反癩病污名對整個社會具有療癒的功效。反觀台灣,這半年來由於漢生病對日求償勝訴而激發關於戰後癩病史的討論,在時機的巧合下不可免於與樂生院保存的論述場域接合,而激起了一些去歷史的或是簡化歷史的論述,這些「歷史」論述還有待檢驗,它們在短期中或能達到媒體效果,社會教育及自我反省的潛質則需更多琢磨!
◎參考資料
潘佩君,2005。〈日本癩病政策的沿革〉。
Sato, Hajime. and Minoru Narita, 2003. “Politics of Leprosy Segregation in Japan: The Emergence, Transformation and Abolition of the Patient Segregation Polic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6: 2529-2539.
本文關於日、韓經驗的部分資訊來自「政府出版資料回應網」收錄1975年至1984年間台灣派遣赴日、韓研習癩病工作者之出國報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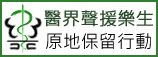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