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樂生療養院、看傳染病隔離的歷史空間 /范燕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疾病空間的知識/權力
近代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是因應近代社會、國家的發展而出現的,特別是伴隨傳染病流行的衝擊而產生。而傳染病控制的基本方式之一,是透過對於帶病菌者的發現(檢 疫)、隔離、治療,相對保護其他公眾者的健康。換言之,隔離空間的設置,成為必要的措施。由於公共衛生、防疫,牽涉公眾的健康事務,它賦予國家公權力介入 個人生活與空間,然而、公權力介入的合理與正當性如何?是否超越公權力介入的合理限度、而侵犯到個人基本人權?這是現代社會極為關切的問題。
癩病(俗稱麻瘋)是人類很古老的疾病之一,由於癩病發病的晚期,患者的外貌產生極大的改變,使其成為最為人恐懼、也最被污名化的疾病。就台灣近代防疫 史觀之,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引進公共衛生措施,近代式的傳染病控制也隨之出現。1930年創立的「樂生療養院」作為慢性傳染病、癩病防治的專門機構, 相較於日治前期殖民政府所處理的急性傳染病,樂生院隔離空間設計,有極為特殊之處,也成為反思疫病空間的重要議題。
台灣在去年(2003)SARS流行期間、發生疫病隔離的新衝擊之後,理解近代史上、癩病這種特殊的疫病隔離空間,也就有其嶄新的時代意義。本文在討 論「樂生院」疫病隔離的空間特徵以及其歷史變動,並思索這樣的疫病歷史空間、能提供台灣社會何種省思。
二,傳染病與空間的權力-殖民地疫病轉型與文明的象徵
傅科(M. 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的開場,談論著西方中古時期痲瘋病的故事。也就是西方中世紀時代,整個基督教世界、痲瘋病院曾經多達一萬九千間,至十 五世紀,多數痲瘋病院卻已空無一人。然而,就在痲瘋病從西方世界消失之際,乘載著精神錯亂者的「愚人船」隨之登場。傅科描述從「隔離痲瘋」轉向「放逐精神 病患」的歷史現象,主要為指出:痲瘋病雖然消退了,但西方人附加在痲瘋病的價值觀與意象,即排斥或恐懼痲瘋,附加其可怕的負面形象,仍然深固的持續著;而 且這種社會心理更轉向排斥精神病患、貧苦流民、罪犯等。傅科實深刻的指出:人類排斥弱勢以及邊緣者的心理結構,有著驚人的固執與延續性。
誠如傅科揭發的、人類排斥疾病有其延續性的心理結構,樂生院之作為痲瘋病隔離的機構,存在值得深究的社會心理。同時,這種對於傳染病的恐懼與排斥的心理, 某種程度也反映在隔離空間的設計,樂生院之成為痲瘋病終生隔離的空間,也不外反映人類對於痲瘋莫名的恐懼。
1895年日本治台之際、已仿效歐洲國家,確立以西洋醫學作為國家醫學的主體,特別是採取德國醫學體制,並且在防治急性傳染病的過程,建立公共衛生制 度。日人治台之初,又遭遇風土疫病流行的衝擊,為減少日人生命與健康的耗損,以及鞏固殖民統治,不僅加強近代衛生設施,也重視傳染病防治。而日文稱為「避 病院」的傳染病隔離所,在1896年鼠疫防治之時、首度設置。
近代國家對於傳染病的控制,以影響迅速而廣泛的急性傳染病如鼠疫、霍亂等為優先。日本治台之後,對於傳染病的防治、也不例外。1920年代以後,總督 府著手如結核病、癩病等慢性傳染病的防治,樂生療養院在1930年正式設立,也是屬於殖民地公共衛生的發展脈絡。
不過,樂生療養院的出現,也非僅是從急性、到慢性傳染病控制的必然結果。相關的背景因素包括:在台灣的日本醫學者提出,在台日人處於被台人癩病感染的 高度威脅,以此警示殖民政府;以及教會醫院、特別戴仁壽醫師對癩病診療、照顧的積極作為。加上,日本「癩病防治之父」光田健輔建言:外國傳教士對於癩病醫 療有影響人心的作用,希望台灣總督府能重視此事,並且取代之。
總之,1930年「樂生療養院」之設置,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除了殖民地公共衛生、防疫重點轉型之外,主是日人在台定居人口增加,恐懼殖民地慢性傳染病 的威脅;以及殖民政府深恐教會醫院對癩患診療的影響太大,而欲取而代之,以展示推展文明醫療的作為。即在這些殖民地政治與社會心理的影響之下,終於出現這 座大規模的隔離醫院。
三,樂生院的空間設計與終生隔離的概念-疾病認知的侷限與過度恐懼
1927年,台灣總督府以三年為期,開始在新莊興建「樂生療養院」,也正式開啟台灣的癩病防治。日本早在1907年公布有關癩病預防的法規,確立癩病 為傳染病而有必要隔離,在全國各地設立五個癩療養所,初步以收留流浪癩患者為主。因此,台灣不僅延用日本相同法規,而且對於療養所的建築設計,也參考日本 熊本九州療養所(現今稱「惠楓園」)與東京府的全生病院(現今稱「全生園」)。
當時日本癩療養所的特點,主要是依據傳染病的細菌學概念,區別為「有菌」、「無菌」兩大部分,以及建設生活機能完整的設施,也是近代日本對癩病採取傳 染病隔離的明確表現。1930年完工的「樂生院」,也具有這些特點。該院於同年12月開辦,正式收容患者,最初僅有日、台籍五人入院。至第二年年底 (1931)收容人數達百餘人,已達到其預定收容的100人。如果以當時官方調查的全臺癩患人數,歷次癩患者調查,皆在六百人以上,相較於樂生院規劃百人 的收容量,顯示官方初步措施以收留流浪癩患為主。
| 就這初期療養所的建築空間,如圖一:從正門進入院區,除正門左側有守衛室之後,全院主體建築呈王字形,王字形第一進「行政廳舍」,開放對外的;從王字形 「中央走道」進入第二進之後,右側是「治療室」,左側是藥局、醫藥室、試驗室;其中,較為特別是從中央通道有一向左叉出的通道,直接通向「藥局」。這樣設 計的關鍵在第二進「中央」的「更衣室」,也就是管制從第二進到第三進的「有病菌區」必須「消毒」、「更衣」,因此為進入「藥局」又避免「更衣」的不便與費 時,即是走左側叉出的走道。接著,從中央穿堂連通第三進,即為重病室,左側可通達禮拜堂、預診室,右側通達「停屍間」。 |
這樣的空間分配,清楚顯示「有菌」、「無菌」的空間區隔,即以第二進「更衣室」為管制點,在此之前的「行政廳舍」是無菌區域。此外,位於遠離院區主體建築的左側,即看護婦(護士)宿舍和官舍也是「無菌區」。
除此之外,凡患者活動的空間都是「有菌區」,包括從第二進中央「更衣室」為起點,第二進左、右兩側醫療空間,連接第三進的中央通道,以及第三進左右兩 側。同時,輕症者住宅位於「重病室」左上方以及左外側,共計四間「患者住宅」,藉山坡較高的地勢,與「重病室」作區隔;另外,在「重病室」右上方、是提供 患者日常生活需要的「浴場」、「炊事場」(廚房)、「機關室」(蒸氣消毒室)。
而這些患者生活的空間又有監視、禁制的設施,嚴格的管制。如院區外圍周邊的「鐵絲網」,以及設置兩個「消毒槽」,一個如前述的、在「王字形」建築中央 的「更衣室」,另一在左側、「預診室」前面,設「守衛」監視之。而就在左側「守衛室」之外,特別開設一「患者通用門」,並另設一條左側小徑為「患者道 路」,直接通到縱貫道路,顯示患者進、出院區都由此特定路線。此外,處理違紀患者的「監禁室」,設在「王字形」建築斜右外側、一單獨空間。
上述的空間設計,無論是「有菌」、「無菌」的分類與空間區隔,或採取戒備森嚴的空間管制,顯示對於癩病戒慎恐懼的心理。然而,從近代醫學、細菌學的角 度觀之,當時日本醫學以及公共衛生學界對癩病持如此戒慎的心理,並非合理之事。
近代所謂癩病(leprosy),是1873年挪威醫師韓生(Dr. G. A. Hansen)因發現癩病原菌(bacullius)證實為傳染病者,並認為強制隔離是最佳的防治措施。然而,Hanson發現癩病原菌之後,在動物試驗 及純培養試驗又呈陰性反應,並不符合近代科學醫學的細菌學原理。其中所顯示的意義,乃是當時部分醫學者所主張的、也是爾後醫學研究證實的,癩病雖為慢性傳 染病、但也是最不容易傳染的一種。因此,對於癩病施行如此嚴密的分類、隔離,不僅是醫學界對癩病認知有限所致,也是因傳統上對於癩病的附加想像,而造成過 度戒備和恐懼的結果。
此外,樂生院的空間狀況有些在圖一並無法顯現出來的,是以照片影像刊載出來的。這些影像不僅呈現癩病患者的日常生活空間,從學習、勞動、娛樂以及宗教 等各方面,說明患者以院為「家」的良好生活;以及新式而進步的醫療設施,宏偉美麗的廳舍建築。整體上,營造出樂生院頗為吸引人的近代醫療,以及文明進步的 生活情境。這些文明醫療與生活情境,實際存在或經由某種想像而傳達,似乎有宣傳效用。
四,樂生院空間變動與帝國政治/權力的擴張-台灣社會的參與建構
基本上,日治時期台灣癩病防治是日本帝國公共衛生的一環,除特殊的殖民因素之外,主要受日本本國公共衛生政策的影響。當1930年代初日本癩防治法修正, 而殖民政策也強調「內地延長主義」,台灣的癩防治法終究也隨之修改。其中,有關公共衛生的連動發展,是加強癩病的強制隔離措施;而反映在樂生院的空間,乃 是院區空間的變動與擴充。這也顯示國家公權力對於人民生活介入的增強。
從樂生院歷年院區地圖觀之,1934年(昭和9年)之後、院區空間開始有比較大的變動。背景因素是1934年台灣總督府公布「癩預防法」,延用日本在 1931年制定的癩防治法規,重視強制隔離措施。因此,樂生院收容患者人數快速增加,院區也隨之擴充。1935年,樂生院收容定額增至227人,1938 年收容定額為587人,然至年底實際收容已增至628人;至1939年收容定額達最高額之700人,至日本治台結束為止。
1931年日本「癩預防法」修正,主要是著重充實防癩經費、從業管制、加強檢疫與報告病例、管控私人相關機構等,這些皆有助於增加國立療養所收容癩患 者人數。而在殖民地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也就是強化警察取締癩患者的權力,及因充實經費而能取代、或減少教會療養所的影響。
同時,台灣總督府為落實新法執行的效力,成立社會事業組織,籌募相關經費與取締方案,樂生院空間因此大幅改變。1933年6月總督府在尚未修正癩預防 法之前,先成立「台灣癩預防協會」,以協助防癩宣導以及促進相關預防設施為目的。該會成立之後,首要措施是推動模仿日本設置小型療養所「十坪住宅運動」, 在減輕官方經費負擔之下,有效擴充樂生院療養空間。
至於落實警察取締癩患一事,除總督府警察部門調查癩患的次數增加之外,台灣癩預防協會也推動,由樂生院醫療人員組織的調查小組,選取各地特定村落、一 般是癩患者分布較多的地區,如澎湖廳、台北州、高雄州、台南州等執行細密的調查,一方面也在檢驗警察部門癩調查的可靠程度,並因此證實其有所落差,而新發 現不少病歷例。
| 據此,樂生院的空間變動,可以1937年、以及1939年兩張地圖分析之。就患者收容觀之,1937年年底患者數是433人;而1940年年底是635 人,幾乎達院區最高容量。首先,就圖二、圖三:1937年樂生院地圖,整個院區的擴大最顯著的,就是經由十坪住宅運動新建的,包括在圖的右上方的「光山 舍」、「漁翁舍」、「雙愛舍」,以及左上方的「婦慈舍」、「喜一舍」、「東高雄寮」,共計六棟。此外,在原來「患者住宅」正上方以及左上方、增建三合院式 的「患者住宅」,共計九棟。院方建築這種三合院式,顯示考量台人居住習慣、或可說是長期療養生活的做法。 |
從1937年的地圖,還可見幾項新增設施,也是「台灣癩預防協會」推動的。包括:正門入口的左側通道上設置「保育所」和「面會人免費住宿所」,「保育 所」也稱「新生寮」,是提供收容未感染兒童之用;以及圖右側的「特殊患者住宅」,也稱為「昭和寮」,提供經濟富裕的患者獨居之用。另新出現的專屬空間有: 「賣店」、「木工部」、「恩賜紀念運動場」。以及在圖頂端的、日本國家神道信仰「神社」,而從院區正中間出現一條「中央路」、直通「神社」,也顯示如此政 治空間的重要性。此外,另有一重要衛生設施是左上角的飲水設施。 |
其次,就圖四、圖五:1940年樂生院地圖,由於此時樂生院已達最高收容量,成為戰後樂生院空間的基礎。此時空間顯著的變動在於:原來的護士與職員宿舍 從偏離院區的左上方,轉移到最右下方,而且宿舍、佔地空間也大為增加;而讓出來的宿舍空間轉為患者住宅,總計新增十四棟住宅。以及左下方有一大片患者耕作 的田地。 整體觀之,在樂生院隔離空間的擴張過程,除為因應患者人數增加而擴建患者住宅之外,充實患者療養生活的空間也隨之增加。這些設施不乏因應台人生活習慣者,當然也具有強化對日本帝國忠誠的政 | |
| 治設施。此外,從當時樂生院大風子油治療成果報告,顯示樂生院也是兼重實驗治療研究的。 | |
無論如何,1934年以至日治結束,樂生院作為癩病強制隔離的機構,透過衛生警察或醫療人員普遍調查、檢疫、監禁癩患的過程,終究造成社會恐懼氣氛,加 深對痲瘋的歧見。當時日本帝國仿效北歐(挪威)的做法,對結婚患者施行節育處理,也是假「公共衛生」之名,即藉著維護公眾社會健康的名義,枉顧癩患人權的 做法。 當時日本對於癩病採取極端的公衛措施,一方面是近代醫學在癩病醫療的侷限,另一方面日本將根絕癩病、視為作為文明國家的必要條件,因此衛生官員重視宣傳癩病毒的危險性,以及對癩患施行絕對隔離、禁絕生育。當時、殖民地台灣防癩措施既以日本本國為依據,似乎 | |
| 較難違抗日本醫學界的主流看法。也因此,樂生院終究成為強制隔離以及終生監禁的機構。 | |
五,反映戰後政治變局與社會偏見的空間:被社會隔離的新院區
1945年日本殖民時代結束,台灣歷經政權轉移。國際癩病防治也轉向新的里程碑。1940年代中期抗癩特效藥、磺化藥物普羅敏(Promin)及戴普松 Dapsone(DDS)的使用,有效抑制癩桿菌。以及1960年研發能完全治癒癩病的Rifampicin與Clofazimine。因此,國際間倡議 新的癩病防治措施,鼓勵採取尊重人權的開放處理,及門診治療方式。
在戰後癩病醫療的新時代,台灣對於癩病處理也轉向新措施,即1954年起、於全台各地陸續設立皮膚科門診、所,非開放性癩患者轉由各地門診管理。然而,新莊樂生院癩患的處遇仍面臨許多難題。
首先,在戰前被強制隔離於樂生院的患者,雖然試圖返回家鄉,然不少人終究因「痲瘋」的污名,社會關係的疏離,而被迫再度返回樂生院。換言之,儘管抗癩的藥 物進步了,但社會大眾對於痲瘋的歧見並未消除,他們僅能退回到原來與社會隔絕的世界。繼之,戰後初期另一波新移民進入台灣,當時撤退來台的軍民之中,發現 不少癩病患者,樂生院仍是主要收容機構,收容人數最多達一千餘人。就此,樂生院成為新、舊癩患者共同的家園。
基於戰後台灣新的政治、社會脈絡,樂生院空間又有變動。首先,戰後防癩措施轉變最重要的象徵,是1954年樂生院方撤除院區四周鐵絲網。繼之,因應從 軍方送來的癩患者,開始增建新病棟,是就原有院區病棟的外圍加以增建。即在1950年代軍醫署、退輔會先後撥款新建軍患病舍,包括:經生、惠生、靜生等。 以及1966年又完成啟用新建盲人病房。1975年,增建新生甲、乙、丙等病舍。這些軍患、榮患病舍大抵是分布在院區左、右兩側外圍,或偏左上角的邊區, 反映作為院區新族群的空間特徵。
在戰後樂生院的新建築之中,最有特色與意義者莫過於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三種宗教建築,這是緣於三種宗教對於院區病友,發揮無比愛心與長期照護。其 中,基督教孫理蓮牧師娘的芥菜種會是最早進入救助病友者,也首先在院區設置教堂,聖望教會禮拜堂(1952年完工),發揮長期救助病友的最大力量。
在聖望教會禮拜堂建成之後,院內佛教徒大為所動,決定動手新建佛堂,由院友金義楨統籌其事,選定當時院區低漥陰濕的空地填土,病友們一磚一瓦將搭蓋佛 堂「棲蓮精舍」,於1954年5月落成。繼之,輔仁大學古神父籌備創建天主教堂,於1971年4月完工。另一由病友同心協力完成的建築、是消費合作社與理 髮廳,於1960年完工,樂生院提供建材、病友自行建造,牆上木板刻字與房頂「樂生」二字皆是病友製作。
戰後,樂生院雖然逐漸脫離作為公共衛生上、癩病隔離療養的定位,然而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它依然被隔離於台灣主體社會之外,即在此意義上、樂生院仍是被社會 隔離的院區。然而,就在這被社會隔離的空間之內,樂生院病友在宗教團體的支持與精神安慰之下,發揮殘而不廢的精神、自力更生,默默的貢獻台灣社會,使這個 院區迴盪著許多他們打造家園、貢獻社會的故事。
六,結語:樂生院與日本人權森林的構想
關於人類疾病史,不少學者指出:疾病雖是一種生物現象,然而人類對於疾病的理解、卻無法自外於其社會文化脈絡,疾病既是生物現象、也是社會現象。生物性的 疾病固然可怕,但人類因社會文化的偏執和恐慌,所造成的疾病迫害,可能比病菌更為嚴重。
人類最古老的疾病之一的癩病,就是這樣受到人類各種偏執所扭曲的一種疾病,無論傳統社會視痲瘋為一種「天刑病」或遺傳病,並如傅科所言、採取絕對隔離 的方式、將其排除於社會之外;或者當近代國家的公共衛生發展之後,以維護公眾健康的的正當性,合理化對癩病患者強制隔離措施;或甚至在戰後,抗癩藥物進 展、患者已呈無菌狀態,但社會歧見仍附加其上,癩患者仍處於社會邊緣。樂生療養院、這樣深刻的銘刻著對癩病偏執的歷史空間,它實提供給台灣社會許多重要的 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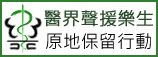





3 則留言:
蔡明洲 陽明大學醫學系七年級
e-mail: blueboristw@hotmail.com
蘇崧南
台北榮民總醫院教研部研究員
snsu@vghtpe.gov.tw
連署樂生
保留樂生療養院,留給樂生居民生活的園地!!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