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院民 湯伯伯 自述人生
湯祥明
民國二十二年生
民國四十年入樂生療養院
未婚,現居住於組合屋
民國二十二年生
民國四十年入樂生療養院
未婚,現居住於組合屋
生長環境,入院經過
我是民國二十二年次的,我的祖父是苗栗人,所以我的父母親是客家人,但我們家就住在新莊,他們說的台語因此還有一點口音,我的客家話只會聽,不太會說說,在樂生院內也沒有幾個客家人,要講也找不到人講。
就小時候的記憶,父親是日據時代總統府的官員,大概相當於現在的衛侍長(侍衛長)。我是在民國四十年,十九歲的時候進入了樂生院,當時我是建中的學生,模樣就是屋內牆上掛的那幅畫像。那時候是強制收容,發現了痲瘋,不來不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得到痲瘋病,一開始我的母親也不相信,鄰居也不可能,因為父親過世以後,我們家是獨棟的房子,周圍還有像圍牆一樣的籬笆圍住,來往家中的人也都是一些軍中的士官,一般人很少接近我家裡,到家中的本省人很少。小時候即使是要出門買東西,也是晚上洗過澡之後由父母親帶出去,很少和別的孩子混在一起,所以是怎麼得到痲瘋病的,實在是不曉得。當時檢查出有痲瘋的時候,我檢查自己全身上下,也實在看不出什麼病徵,我的母親也看不出來,醫生說,痲瘋菌是潛伏在身體裡,不是一時之間馬上發作表現出來,有的病人是三年、八年,甚至十年以後才發作出來。
我會檢查出痲瘋病,是因為一位在日據時代待在樂生療養院醫院裡面研究室,專門研究痲瘋病的醫師(賴尚和),由於光復後樂生院內的情況混亂,這位醫師不願意繼續待在院內,就到台大去。那時候師大、台大、建中三個學校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學校檢查學生,並不是大規模的一一檢查,而是偶爾挑幾個來抽檢。他是位對痲瘋病相當有研究的醫師,當時我在操場上,和三四個同學在一起,他就看見我,先來摸耳朵,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在摸淋巴,接著是摸乳頭,還有(手肘)關節也摸一摸。他當時搖了搖頭,並沒有說什麼話,但可能有告訴同學,當時大家聽到痲瘋病,笞疙兩個字都害怕得要命,我上學的時候漸漸覺得同學們很奇怪,平常很接近我的怎麼很害怕的樣子,很有距離。那時候因為交通問題,我家雖然在新莊,但我是住三重,一個星期後,母親從新莊到三重來問我:「最近學校有發生什麼事嗎?」我說沒有,和平常一樣。母親又問:「最近有醫生到學校去嗎?」我說有,有一個台大的醫師到學校來。母親說醫生告訴他,我體內有痲瘋細菌,痲瘋病,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此後我到學校去,感覺同學很冷淡,還告訴我母親說,醫師說我得了痲瘋病,不能再上學,但是當時已經念到二年級了,要把學業放下,怎麼放得下呢?那時候每日走到學校,到大門的時候,想進去也不是,想回來也不是…有一天我想開了:唉,這樣子念下去還有什麼意思?同學看到你,好像一個活老虎坐在那邊似的…啊,不念了!那一天我就回過頭來掉了眼淚,不念了。往後當我到了樂生院內以後,即使後來開放,可以出入,但是我到台北都不想再去建中那裡,那條路我都不想再過去,建中門口我都不想再過去了。
後來我就來到了樂生。賴醫師對痲瘋病的了解很徹底。依我在樂生問過很多老病人,那時經濟情況不好,很多病人都穿得破破爛爛,我看到很多病人的乳房都像女孩子一樣腫脹,那時才想到,賴醫師抓我的乳房的意思。一些老病人告訴我,痲瘋病人的乳房,有個腫核,像龍眼那麼大,一般發育時男生的這個腫塊會化掉,而痲瘋病不會化掉,細菌都積在裡面。
後來我就來到了樂生。賴醫師對痲瘋病的了解很徹底。依我在樂生問過很多老病人,那時經濟情況不好,很多病人都穿得破破爛爛,我看到很多病人的乳房都像女孩子一樣腫脹,那時才想到,賴醫師抓我的乳房的意思。一些老病人告訴我,痲瘋病人的乳房,有個腫核,像龍眼那麼大,一般發育時男生的這個腫塊會化掉,而痲瘋病不會化掉,細菌都積在裡面。
我不是自願進院的。那時候是強制收容,知道你得了病以後,他有方法的,樂生院內的指導所,會同你所住的地方的衛生所,就算在你家找不到你,他們每天開著寫著「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字樣的車子到你家裡去等你,鄰里上最討厭這樣的一台「苔疙車」,他們連續一兩個禮拜天天來宣傳:「某某某得了痲瘋病,大家快勸他入院,不然全村的人都會得到痲瘋病…」逼得你無路可走,只好乖乖的來到療養院。他們天天來,我當時因為念書住在三重,母親也跟我說:你自己做過決定吧!我覺得煩了,就說:「你下次叫他們等我吧!我再去醫院做檢查。」我從三重到新莊的時候,他們就開著車在我家等我,拿了手銬像抓豬一樣把我押進車裡,我就常說啊,要是那個指導員讓我碰到,我一定要活活地把他打死…我都已經承認我有痲瘋病,乖乖的要跟你走了,為什麼還要這樣對我?他們那時候專制時期,就是這樣子帶過來的。
還有硬抓的啊!我來的時候是民國四十幾年,一共來了三批人,一批有四十幾個人,一批是民國四十一年時,金門來的;一批是陳再添他們小港來的,還有一批是台南和澎湖。這之後就沒什麼強制收容了,但到底是不是最後一批,我不記得了。那時候來是在桃園火車站,火車上寫著「痲瘋專車」,由警察顧著,再趕上卡車,人下來了以後,車子就馬上進行消毒。剛到樂生院時先進行抽血,做抹片檢查。
有一次我和院長開玩笑,院長說開放了要我們出院,我說:你講的這是什麼話?當年你們把我抓來的時候,我是現在這樣子嗎?沒有醫藥可以醫治,病體變成這樣,你叫我回去,這是什麼話呢。不過說實話,當時就算有醫藥,病人也很多是無心治療的,看到到處都是鐵絲網,還有「以院作家,大德曰生」的牌子,看了都會掉眼淚的…現在患者和捷運公司爭執的事,當年你明明告訴人家,病好了你就身體好好的出去,就算病沒好,這裡永遠是你的家園。那時候即使是死了也不能把屍體運出去,要帶去這裡的山上燒,放在這裡的骨灰塔,病人會認定這裡的。
還有硬抓的啊!我來的時候是民國四十幾年,一共來了三批人,一批有四十幾個人,一批是民國四十一年時,金門來的;一批是陳再添他們小港來的,還有一批是台南和澎湖。這之後就沒什麼強制收容了,但到底是不是最後一批,我不記得了。那時候來是在桃園火車站,火車上寫著「痲瘋專車」,由警察顧著,再趕上卡車,人下來了以後,車子就馬上進行消毒。剛到樂生院時先進行抽血,做抹片檢查。
有一次我和院長開玩笑,院長說開放了要我們出院,我說:你講的這是什麼話?當年你們把我抓來的時候,我是現在這樣子嗎?沒有醫藥可以醫治,病體變成這樣,你叫我回去,這是什麼話呢。不過說實話,當時就算有醫藥,病人也很多是無心治療的,看到到處都是鐵絲網,還有「以院作家,大德曰生」的牌子,看了都會掉眼淚的…現在患者和捷運公司爭執的事,當年你明明告訴人家,病好了你就身體好好的出去,就算病沒好,這裡永遠是你的家園。那時候即使是死了也不能把屍體運出去,要帶去這裡的山上燒,放在這裡的骨灰塔,病人會認定這裡的。
院內早期醫療、隔離
在那個沒有醫藥的時代,說句難聽的話,病人都是在等死而已。那時候根本是沒有醫藥的,集中到這裡關起來而已,四週都是鐵絲網,一被關進來就出不去了。你們剛剛進來的門口,有經過一個崗哨,再進來是大禮堂,以前就在那個大禮堂的斜坡下面,阿兵哥拿著刺刀在那裡,再跨一步就開槍,當時病人的活動範圍就到那裡。民國四十年的時候有鐵絲網,四五年之後才慢慢撤掉,雖然撤掉了,但管制仍然很嚴。事實上當時的病人也不敢跑出去,連在站牌下等車都不敢,旁人一看就因為是痲瘋病而嚇到、非議,憲兵看到就馬上帶回去關緊閉了。
當時真的是沒有醫藥,一天到晚有人在自殺,自殺像是流行的一樣,今天這裡有人自殺、明天那裡有人自殺,天天都有的…因為神經痛痛得受不了,很多人因而走了極端。我剛開始進樂生院時是完全看不出來有病症的,我的發作則是很慢的,不知不覺很慢的進行著,像是我的手,去年元月份還可以拿著畫筆,到了五月份,痛風一來,就沒辦法了。有些人發作的很快,天天晚上都在神經痛,快的時候一個晚上手指就彎曲了。回想起來,樂生當時的醫藥環境,病人實在是太可憐了,那時醫院內最好的藥就是阿斯匹靈,而醫院的藥房就是一些日本人走後留下來的,沒什麼療效的大風子油,病人拿大風子油不是拿來治療,而是帶回去當作燃料點火用。擦外傷的藥也有,紅藥水、黃藥水、碘酒這三項,沒有消炎藥。那時候是用破掉的被單,撕下來再接起來,當作繃帶,用完並不丟掉,還要捲起來洗一洗、晒乾再拿來用,以現在的角度看當然衛生是不合格的,但當時也只得用。那時候病人的外傷很多,身上很多傷口,有的整條腿都是,你們看到一定會嚇到,我看到我都怕。所謂的醫療,就是每天為這些外傷的病人換藥。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正派的醫師,我告訴你這些醫生的來歷好了,抗戰結束後,過去在日本人軍中的一些衛生兵、醫護官,懂得幾個英文字,就來樂生療養院當醫師。當時多好笑呢,醫生看病時,就雇一個病人在門口叫號:「某某某、幾號」這樣,病人走進去以後並不是像一般醫師拿聽診器聽診啊等等,而是醫生直接問你:「你要開什麼藥?」病人都把藥房裡面的藥記得很清楚了,要開什麼藥像是碘酒啊、紅藥水啊,就自己告訴醫生,醫生就把藥給病人。護士也不是像現在由護校畢業,而是一些鄰近地區的女孩,小學畢業以後,有些人事關係就進樂生療養院當護士。病人之間都會說笑話,哪裡的護士最強?樂生療養院的護士最強!拿病人當練習,打針一插就插十幾次,打針最厲害。病人都會挖苦說,這裡的護士打針最強,其它的什麼都不懂。她們不是真正的護校畢業的,就是這樣一路混,混過來的。當時醫院的環境,不要說不讓你們過去看了,就算讓你們去看你們也不敢,環境髒兮兮的,很嚇人。醫生到了院區看了病人,都要過消毒池,包得緊緊、裏得密密的,民國四十年的時候都仍是這樣。共有三個消毒池,在治療科這邊往上到王字型那邊,後來改成牙科的地方,有一個消毒池,指導所現在還沒拆,圍牆留了一個縫,也有一個消毒池,大約四十、六十見方,整天放了消毒水;行政大樓那邊的小池子不是消毒池,是後來沒做好的焚化爐,病人是不能走到行政大樓去的。一直到民國五十四、五年時的院長,當時已經知道痲瘋不會傳染,院長慢慢也想開了,才把消毒池填掉,管束也漸漸放鬆。但病人都像關在籠子裡的鳥兒一樣,你叫他飛,也不想飛了,讓他出去,也不出去了。到後來民國五十九年的時候,當時的院長是游天翔院長,(他是我來了之後的第二任院長,老院長剛走。)他是個很仁慈的人,他看樂生院裡面的院民,好多都是人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埋沒了很多人才,的確是這樣,當時還有已經念到大學二年級的病人,但是大家不願意出去,是因為畏懼出去了以後,如果又病發了,那怎麼辦?所以游天翔說過這麼一句:「現在醫院裡經費不夠啊,所以你們要出去自力更生的人,或是要出去念書的人,你們出去好了。萬一病況有什麼改變、發作的話,照樣可以回來住院。」所以病人就比較有勇氣出去了,像是去師大念書啊,當記者的也有,當船長的也有,還有人當過警察局長,大家慢慢出去了。腳手好一點的人,就很少再回來了。那時期開始有DDS了,他們就偶爾一個月、半年回來拿藥。
全世界也沒有一家醫院,病人進院身份證要沒收的。我們當時也沒有選舉權的,一進來出生地的戶藉、住所的戶藉等都被滅掉了。現在你去查,我是樂生院出生的,怎麼查也查不到原來的戶藉了,是集中放在這裡管理。後來有了身份證也是政治問題,有個張德發要選新莊市長,新莊街上也分成了兩三派,就讓樂生院裡的人全都投他,後來他選上了就有人說他是「笞疙鎮長」,是靠樂生的票軌選上的。那時候院長說要投給誰,大家都要乖乖的投給他,指導員就在旁邊看你,有沒有乖乖的投給誰,白色恐怖的年代就是這樣。還有一個笑話,一個叫楊丹的女人,小時候得了痲瘋病,本來住在樂山院,因為那是私人的機構後來解散,她就來了樂生,碰上了選舉。她到處問說,要投給誰呀?也沒人敢吭氣,她因為痲瘋病都關在家不敢出去,沒念過書也不懂,乾脆就通通蓋印下去,最後就這張票最特別!通通有獎!哈哈,後來院長追查出來是她,她也只好說:「你們又不講啊,我又不知道該投誰…」選舉權大概也是民國四十五年左右的時候開始的。身份證也很奇怪,沒貼照片。因為當時照相並不容易,要特地去外面的照相館照,照相館根本不願意替病患照相,叫他來樂生他也不願意來的。院方則是有詳細的資料,從入院時就有紀錄,所以院方都還是可以管理的。
DDS
DDS很早就出現了,比這個時期早得多,大概民國四十五、六年的時候,病人可以發到。但剛開始的時候藥很少,用抽籤的,一天抽25個人。吃DDS糟就糟在哪裡呢?英國人發明DDS的時候是針對英國人的體型,他們體型大、營養好,(台灣的)醫院根本就不懂,也沒有明文告訴病人怎麼用藥,很多人得了DDS以後,很心急,今天吞、明天也吞,不吃還好,一吃更糟。藥會破壞血球,引起神經痛,痛止不了,所以跳水死的、切腹死的,自殺就是這樣來的。藥本來是用來治病的,最後病人卻害怕起DDS,不敢吃藥。那時營養不好,一天七毛五的補助伙食費,而豆腐乳一塊就正好七毛了,買不了什麼東西。所以很多病人不想要治療,如果有人要吃藥,老病人還會說消極話取笑:「十年前,十年後。」意思是說十年前還很年輕貌美或俊帥的,十年後也因得到痲瘋病而不會好了,要好、要離開,就從燒病(死)人的地方離開吧。所以當時就是這樣消極、不想治療的風氣。醫院應該要告訴病人怎麼使用DDS的,但是,根本沒有嘛。後來有人發現吃DDS喝酒的話,會要人命的,這下可好啦,就有人開始屯積DDS,偷偷留起來,遇到不如意的時候,就當作自殺藥來用…哈哈,說來好笑就是這樣…唉。
DDS白色,小小顆的,咬在嘴裡也沒什麼味道,但這個藥非常奇怪,外面的人有些家裡有孩子,長了癩痢什麼的,求醫也求不好,就拿DDS來試試看,狗的皮膚病也是這樣,一吃下去就馬上好起來。現在的DDS已經改過了,我忘記過去是多少gram了,但過去是現在的四倍。很奇怪,有的人一吃下去馬上就發作起來,發冷發熱啊、沒辦法適應,有的人不死心,吃一顆不行,就試半顆,再不行,就吃更少,慢慢試出劑量來。現在吃藥的方法,可以自己去開,一次就是開一個月30顆,一天吃一顆,不過吃多了、吃久了還是不舒服,會貧血頭暈暈的。病人發作是這樣的,和免疫、天氣等都有關係,我兩個月前也是不太舒服。所以病人大概一個星期吞個一顆兩顆,是比較好的。過去很多日據時代就開始得病的老病人,身上腿上都很多外傷,稀稀爛爛、還流血,說那些傷口能好很難相信,但是碰到DDS就真的都好了,問他有用別的東西嗎?也沒有,只吃DDS就夠了。DDS也沒有抗藥性,並不會越吃越重。
剛剛那位伯伯(李添培),他是和裡面的院民結婚,兩個人都是患者,生了小孩以後就很擔心女兒會不會得痲瘋,讓女兒從小就吃DDS,後來好像也沒事。就我的觀察,很多患者結婚生下來的小孩,幾乎都沒有得到痲瘋。
症狀
斑紋初發的時候,大概就像一塊錢銅板那麼大,圓圓的,紅紅的厚厚的一點,有點高高的,這是和生癬不同的地方。斑紋可分為兩種,白的和紅的;白斑紋不容易看出來,衣服脫起來仔細看也不一定看得出來,就像一般皮膚長得白斑,顏色比一般皮膚淺一點,但也不容易散掉,難醫,紅斑紋比較好醫。還有另一種「節枝」,一節一節的,吃了DDS以後會炸(裂)開,流膿血出來,慢慢的傷口再好點。有斑紋的病人較多,有長節枝的病人比較少,大概十個裡面只有三個人有。長斑紋並不會痛,但是慢慢的從還有感覺,漸漸就麻掉,沒有感覺了。一般病人在病發的時候,可能是外傷沒有注意,流膿了,會發冷發熱,是從五臟六腑發出來的,高燒可以到四十一度,發冷的時候怎麼暖都沒有用,牙齒甚至會喀喀喀的打顫(chills),這時候就趕快找,看看是哪裡有外傷引起。病人病久了,自己都可以當醫生了。
我的手也會神經痛,痛起來也會鬼叫鬼叫,沒辦法伸直,關節都會腫起來。手指因為麻掉,很多病人都是這樣,因為麻掉會受傷,慢慢的就一節一節(從末稍)開始斷掉了,我剛進來的時候手都好好的,慢慢的彎掉,手指的肌肉(魚際肌)也會萎縮掉。院內的病人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神經質,手腳會彎曲,痛壞掉,臉孔比較好看;另一種是皮膚質,會長外傷、眉毛會掉等等。你們也可以注意,通常比較沒有外傷的病人,就是比較會神經痛的。雖然明明醫院都檢查沒有細菌了,但是偶爾還是會發作,所以最好還是想到就吃一下DDS,但有的人一吃就不適應,會發冷發熱(副作用)。現在還有一種他們叫「黑藥丸」,吃下去皮膚會烏黃。神經痛發作的時候,會痛到在地上打滾呢,也沒有一定在什麼時候發作,和個人的體力和健康狀況有關係,身體比較虛弱的時候,就容易有神經痛。至於我其它的關節痛,是年紀大了的老毛病了。
至於皮膚質的,五官壞掉也是免不了的,樂生裡面很多人戴著墨鏡,因為十個有八個睫毛也會掉,掉了以後很怕風沙和陽光,像我的右眼也是,因為神經炎而不容易閉合,因為怕風沙所以戴著墨鏡。另外痲瘋病人的皮膚很多麻掉的地方都沒有毛孔,你們可以摸摸看,都很光滑,但有時候天氣涼涼的,反而是一直流汗,因為沒有毛孔的部分不流汗,而別的有毛孔的部位反而特別會流汗(代償)。麻掉的部位是外面沒有感覺,但裡面很痛。我的鼻子是好好的,但有的病人細菌跑到鼻孔裡面,流膿發炎什麼的很臭啊,那時候早上起來他們刷牙洗臉,一漱口、擤鼻涕就都是血,久而久之鼻子就塌掉了,有了DDS以後鼻孔臭的人好像也沒了。
痲瘋傳染力
關於痲瘋病的傳染,我問過好幾位醫師,其中一位趙榮華醫師,他本來是在八里的樂山療養院,後來到了樂生來當到了副院長,因為樂生的人事太亂,他不喜歡,最後去了馬偕醫院。他是個很用心的醫生,樂生的患者去找他看病,他還認得是痲瘋患者的話,第一句話就先問:有沒有吃DDS?沒有吃藥控制的話還看什麼病!是這樣的…
我曾經問趙醫師說:「是不是日本人當時的藥學比較差,發明不出控制痲瘋病的方法,因此只好隔離呢?而且宣傳得那麼厲害?」他笑了笑說:「也許你可以這樣說吧…」痲瘋病當時也是沒藥醫的。我也問過他,為什麼鄰居、旁人的居住環境髒兮兮的,都沒有得痲瘋病,我家整潔乾淨,我卻得了痲瘋病?他給我的答案是,一般人的體內都有癩桿菌,只是會不會發作而已。我也問過樂生療養院的游院長,他曾經開玩笑說:「也許三十年後我也會發作痲瘋病!」他的意思也是一樣的,每個人體內都有癩桿菌,是因為免疫力夠,才沒有病。就像我看院內很多患者懷孕、養小孩的時候,有時候也把食物在嘴裡嚼爛了再給小孩子吃,說起來是很不衛生的,但在院內混大的小孩是很多的,也很多大學畢業等等的。可是都沒有得痲瘋病。我也問過,這樣子實在不像傳染病啊,但它的確是的,尤其是在病人發作的時候,傳染力最強。發作時病人體溫相當高,可能高到(攝氏)四十一度,這時菌量最多,也很多在表面,這時候就不能接近免疫可能比較差的小孩子了,但其它的時候就沒什麼關係。
過去對痲瘋病的宣傳太厲害了,護士看到病人都不敢接近,連門把都不敢碰,現在就不一樣了,病人燒的菜也敢吃了!對痲瘋不了解,就是這樣…
我進院後沒有做什麼工作,院內也沒有什麼工作可以做啊。我就吃飯、睡覺,晒晒太陽,這些書是帶進來的,我喜歡文學,以前書更多的。是因為上面拆掉,東西都來不及搬,書只剩下這些,太可惜了。他們深怕病人又住回去,一下子就房子拆掉了。
我來樂生以後住過的位置很多,一開始是住院長室下面的家屬接待所友愛舍,因為院方沒有管理,很多人打麻將,吵得受不了,就搬去廚房上面的大餐廳,因為後來院長希望餐廳有供餐的功能,就搬去福壽舍和佛教會的會長(金義禎)住在一起,後來大概有人去和院長打小報告,他不願意我們這群念書的人住一起,怕我們結黨,又要我住去平和舍,因為日式木造的房子快倒塌,又搬去新建舍,因為房內有人是精神病,待不下去只好又搬去新生舍,因為我的書太多了,別人的衣櫃放衣服,我的衣櫃都放書,後來蓋了一百號,陸希超院長說房子不夠的可以搬去,我就搬去一百號,因為捷運施工,又往台南舍搬,又再次因為施工的問題搬來了組合屋。搬這麼多次還不算稀奇啦,有人搬得還比我更多的。
大概在民國五十九年,游天翔院長的時候,當時我的腳指頭都還好好的,院方開放出去,我也很想出去,就在外面的工廠找了工作,我和工廠主人的兒子談好條件,他們希望我去工作,我答應了,但是星期六星期天要休息,休息的時候可以畫畫、四處去玩。有了錢以後又可以去台北重慶南路的書店街,以前人家介紹我看的書,和我想看的書都可以買了。我會和人吵架也是因為這樣,你要人搬家,我搬了。可是你今天講,明天就拆,房子拆了心多痛啊,我有好多書都這樣埋掉,他們說想辦法賠嘛,你要怎麼賠呢?心愛的書要怎麼賠呢?過去的櫃子裡都是書,上面也堆著一疊疊的書,還有一些週刊的資料,也都放在我這裡。以前人家都開玩笑說我是書呆子。
這些你們看到的書為什麼還沒有被埋掉,是因為都放在桌子上,收拾都來不及,連桌子一起搬下來的。我最心痛的是一塊硯台,再好的硯台用錢去買可以買到,但我的這塊硯台是國寶級畫家送我的,這是個紀念品,錢也沒辦法買到的。有記者問過我,過去我牆壁上的字畫呢?也都來不及了,房子一拆就全部埋下去了,現在手拿筆很難受,就不想再畫了。牆上的那張十八歲的模樣,也是我自己畫的,因為那是我來醫院的模樣,就是穿著這套衣服,最有紀念性。過去畫了很多荷花、梅花、竹子,人像也有。一般畫的荷花都是盛開的,我畫的都是含苞待放和凋零的,四年前,醫院裡說要辦文藝走廊,一位過去念藝專的護士張心玫就來和我借畫,過去痲瘋病人的畫沒有人想要,我的畫那次就借出了。她看了我畫的牡丹花、荷花看了很喜歡,就來和我要,拿去送給她兒子在新加坡的老師,老師也都不相信竟然是個病人畫的,不是三兩年功夫就畫得出來的。他說看了畫就知道作者心中有些不如意的事…
我的畫之前院長有建議說可以去賣,好歹賣一些錢,就用箱子裝了好多放起來,也想去看看畫現在怎麼了,聽說房子會漏水,過了這麼久,大概也損壞了不少…過去還有新莊民眾服務社的大國父像也是我畫的。是新莊市長張德發和我聊天時拿去掛的。福利社上面的字樣也都是年輕的時候設計的、寫的,我慢慢用鐵絲弄出來、金剛石磨出來的。我的畫法還有四個字留下來,就是迴龍寺修廟,佛教的寺廟要寫什麼我也不知道,就給它寫了草書的「法海、祥雲」四個黑字,題在大殿邊上的兩個小門上。其它寫在紙上的都被埋掉了。
每個人在院裡的感受,和生活的點點滴滴都不同,你們如果去問,病人都很願意說的,進來的時候怎麼樣、在裡面過什麼生活,都很清楚的。
每個人在院裡的感受,和生活的點點滴滴都不同,你們如果去問,病人都很願意說的,進來的時候怎麼樣、在裡面過什麼生活,都很清楚的。
樂生口述歷史工作坊 馨頤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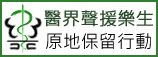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