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療養院員工眷村與我 (台大醫院病歷室主任退休 賴麟徵)
樂生療養院員工眷村與我
台大病歷室主任 賴麟徵 2005.08.16
樂生設立前的癩病機構
根據家父賴尚和先生所著的《中國癩病史》,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前已有小規模的癩病病人收養機構,當然這些機構並非以癩病病人為主,主要收養對象是無依無靠的老人及殘廢等。當時醫藥技術、觀念都不發達,癩病者多因醫藥費浩繁而破產,或因久病以致受家人歧視、冷遇而徬徨街頭,且因形容醜惡、汚穢受人嫌棄,只有靠收養機構收養。「養濟院」原非專為癩病患者而設立,但是就當時的情形來說,顯然成為專收癩病為主的機構。
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與大陸交通受到限制,但在此之前台灣居民以原住民、台灣人及後來的中國大陸來台移民為主。中國大陸移民者大多來自華南,而華南多癩病,這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情。所以在台灣癩病病人大多數為台灣人與從華南一帶移民來台之大陸人;原住民最少,平埔族方面只有在常與台灣人接觸者中偶而發現。台灣割讓給日本後,自日本移民到台灣的日本人也有不少癩病病人,其中由沖繩來者不少。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救治癩病設施一時中絕,以致病人只有徘徊於路旁,或盤踞於廟宇。
1901年台南新樓醫院第四任院長Dr. Maxwell(英國人),看到台灣癩病病人很多,且無適當診療機構,於是該院特設癩病門診,此為台灣現代(西方醫學)治癩之始。後來彰化基督教醫院、台北馬偕醫院,亦相繼開始小規模之癩病診療部。
1925年,當時馬偕醫院院長Dr. G. Taylor鑑於台灣救癩事業之需要,在本省各地與國外東奔西走,前後8年募款建院。後來之樂山園,乃戴氏努力之結晶。
日本統治台灣後,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終於在1930年(昭和5年),鑑於世界對癩病問題之熱心及環境之要求,遂選擇當時台北州塔寮坑頂坡角設新式癩病療養所(即現今之樂生療養院),並發佈「台灣癩療所官制」。此期間癩病防治之基礎得以進行,多賴日本皇室尤其當時皇太后(貞明皇后)之獎勵與支持。可能由於日本皇室之贊助,該院佔地廣大,設備新穎完善,無論病人的照顧或員工的福利都很好。
賴尚和醫師與樂生之緣起
據家父於台灣大學醫學院申請退休時所提出之資料,以及日據時代《台灣名人錄》的記載,家父從當時的台中中學園考入台北醫專預科,大正14年(1925年)3月31日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旋即就任日本大阪商船的台灣東海岸定期航運的船醫。當時台灣醫專的畢業生,一畢業就競相投入開設醫院、診所等賺錢的工作,很少人選擇做船醫。大正14年(1925年)10月25日家父考取台灣醫學得業士後到日本念書,大正15年(西元1926年)3月25日畢業於日本醫學專門學校。由於當時台灣醫專畢業生,與日本正式中學畢後進醫學專門學校比較,資格可能差一點,因此到日本進修博士學位者,都要經過類似的補修學分過程。根據《台灣名人錄》記載,家父自大正15年(1926年)5月至昭和6年(1931年)5月,在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部專修科及附屬醫院真下教授的內科就職研究,同時也到該校理學部小松教授的有機生物化學研究室從事研究。昭和6年(1931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回台灣就職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台北更生院,從事鴉片上癮者及慢性嗎啡中毒者之矯正工作,同時以講師身分任職於當時的台北醫專杜聰明教授研究室,做中藥的實驗治療學的研究。在昭和8年(1933年)11月8日以高等官七等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府癩療養所醫官。
樂生員工眷舍的環境
本人是民國21年(1932年)出生,所以是1歲以後才開始在樂生療養院眷村生活。最初搬去的眷舍是我們老眷屬所謂的舊眷村,後來大概是員工增加,病人也增加,才搬到新建的眷村。所謂新眷村就是最近為了捷運擴建拆除的眷村,舊眷村與新眷村的直線距離約為1公里。舊眷村建在一個山坡地,後院靠著坡度很大的山坡,因有鐵絲袋放大圓石所做的防護,那個時候沒有感受到土石流的威脅,但不曉得目前的情形如何。本人記得有一次颱風,家父關了所有的雨戶(日本房屋窗外一種防風雨的木板套窗),當時情形是還好。
眷舍前面約40公尺的地方有一個小型兒童遊樂園,記憶中有滑梯、鞦韆等設施,附近也有好幾間同樣的眷舍,房子就目前的標準來說相當大,我也去玩過。由那兒遠遠地可以看到火車行走,但聽不到聲音。療養院臨縱貫公路,看得到公路局巴士,那個時候我們稱它為局營巴士,在樂生療養院附近有巴士站,可以搭巴士到台北市新莊街。
本人大約5歲,快要上小學的時候遷到新眷村,據說舊眷村就讓給病人住。新眷村也是建在山坡上,但是坡度較小,後面約1公里的地方有個小山,坡度很大,小時候嘗試爬過,但因坡度太大都沒有成功。我不知道現在捷運施工,這樣的坡度將來會不會造成土石流。小山下有幾戶農家,是標準的台灣式農家,農舍的周圍有竹林,也有一座大水池。本人稍為長大後時常去水池釣魚,大概這些農民不歡迎我們去釣他們養的魚,所以在池中放了不少帶有枝葉的竹子,子常被竹葉住,魚消耗量很大。另外池中也有很多烏龜,烏龜釣到了也沒有用,但常發現魚都在烏龜食道深處,不容易拿下來,也是漁夫的損失。
新眷村的平面配置是最上面有三間高等官的眷舍,然後是幾間判任官的眷舍,記得判任官宿舍裡面曾住了一位藥劑師,再下去就是判任官的行政人員宿舍,最後就是包括工友的一般人員的眷舍。眷舍區與縱貫公路中間有稻田,左側為院長的官舍,其地基很大約有500坪,與當時台北市的官舍比較,也算是大官級的官舍。院長官舍對面有相當大的護士宿舍,可以住20幾位護士,所有的宿舍、眷舍都是平房。由於家父是醫師而且官等高,配住的是高等官眷舍:房子很大有客廳、廚房、浴室及大小房間共6間。當時我們5個兄弟姊妹,連父母共7人,房間足足有餘。客廳舖木板,其他房間則都是榻榻米。另外還有一間倉庫,及一個很大的庭園。父母在京都住了將近6年,哥哥及姊姊都在日本出生並上過幼稚園,但是並未要求我們吃飯時要跪坐在榻榻米上,而是用飯桌坐椅子。前幾年本人旅遊日本時發現無法跪坐在榻榻米上好好的吃飯,飯後也幾乎站不起來。
總而言之日本人很可能認為這些病人需在這裡住很久,所以對癩病療養所的設備要求很高,對病人的照顧很週到,讓他們起碼能過著有尊嚴的生活。對員工的福利也很不錯,有些眷舍可以比美台北市青田街一帶日本人留下來的教授宿舍。這個眷村的20幾個眷舍中,我們是唯一的台灣人,當時家父是療養院院長以下的最高官,家母很好強又愛面子,為了維持台灣人的面子,不讓日本人看不起,所以相當講求庭院的整理,花費不少錢將後院佈置得很優雅,有假山、小池等,小池裡還養了不少我們釣回來的魚。
醫療設備與社區服務
雖然有這樣好的設備及環境,據說在家父來療養院服務以前,也聘請過5、6位台灣人醫師,但都只待了3、4個月,最長不過7、8個月就離開了。家父自學校畢業後,一直持續寫學術論文的研究生活,所以像樂生療養院般研究、醫療服務的生活很適合他。日本政府不僅在樂生療養院收容癩病病人,還設置一個研究室,鼓勵醫師利用院中眾多病人做研究,這是外面醫學部、醫院做不到的事情。這個研究室大約40坪,在連結的小木屋裡擺滿各種人體器官的標本,也有嬰兒標本,家父常在小木屋中解剖研究猴子。研究室裡有1台電冰箱,就目前來說是古董型,冰箱上有鐵片材質圓筒型的東西,不知其作用,但是那個時代介紹電器用品的書中,所介紹的電冰箱就是這個型式。那個時代根本沒有冷氣機,整個療養院包括眷村在內,這是唯一的電冰箱。當時一般人所謂的「冰箱」,需老遠跑到新莊街買冰塊放在其中,電冰箱對我們來說很奢侈,恐怕眷村裡還沒有人用得起這種東西。研究室裡還有保溫箱,切片機、顯微鏡等,實驗台上有手動離心機及各種各樣的玻璃器具。
雖然樂生療養院沒有門診也沒有急診部,只有個小診療室,但是醫師似乎有義務為附近居民看病,大部份是到病人家裡往診,附近有不少小溪流,往診時都是由病人家屬背著醫師過溪,現在除非高官貴人否則醫師到家看病是做不到的。有一次我晚上牙痛,療養院內沒有專任牙醫,兼任牙醫一個星期才來一次,結果哭了一夜,第二天哥哥才帶我到新莊街拔牙。當時樂生療養院的所在是很鄉下的地方,和現在的新莊建築物大增之後完全不一樣,夜間出去往診都要穿長筒靴以防被蛇咬,所以家裡都有幾雙膠皮長筒靴。二次大戰開打後,日本政府實施很嚴格的燈火管制,不能用手電筒。父親自己自製木板的燈籠,裡面放油燈,可以做360°的迴轉平照、下照等各種角度的照明,但是不很亮,只能照到1-2公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有段時期整個療養院只有院長和家父兩位醫師,而附近的居民(大部份是務農的台灣人),都會找可以用台灣話溝通的家父。本人不知道這樣往診是否收費,但好像對周圍的居民沒有收費。
當時瘧疾特效藥奎寧系列的藥物很難買到,日本政府不知是否把這方面的特效藥只交給特定的醫院。樂生療養院沒有門診制度也沒有一般病人之住院病房,所以台灣流行登革熱和瘧疾時,有段時期樂生療養院把一間18個榻榻米大的員工值班室改為瘧疾病人的住院病房,好幾位病人睡在一起。父親回憶那時候說,由於這個原因,他也變成瘧疾驗血的高手。後來有位堂哥從日本學醫回來擔任該院的醫師,最近他的兒子-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回國後在療養院做過一段時期醫師。
院內的休閒娛樂
從縱貫公路進樂生療養院眷村的小路旁邊,有一塊曬穀場面積最少有300多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每逢新曆中秋節-日本人稱此日為「賞月日」,平時農民利用該地曬稻穀,我們則利用該地賞月。那天員工每人帶些酒菜到那兒聚餐同樂,唱歌跳舞(當然不是交際舞)同樂一番。我們小孩子當然也參加,但是很快地就累得睡着了,回家時都是由父親一路背著到家。這個節日在二次大戰期間燈火管制開始後就停止了。
當時有不少宗教團體在聖誕節、浴佛節,派人來院舉辦表演節目慰勞病人,療養院也很歡迎他們。該院有一間二層木造大禮堂,院方會放映電影,日片、洋片到台灣片都有,有時候也請日本歌舞團或台灣歌仔戲團來表演。我們員工眷屬坐在二樓的榻榻米,一樓為病人觀賞區,能走動的病人都會來觀賞。大禮堂的後面有一個運動場,員工在那兒打棒球,也開過員工運動會,這個運動場,可能是目前的基督教教堂的所在。我們也曾在那個大禮堂開過演藝會慰勞病人,記得有一次家父出來唱歌,好像由我跳日本劍舞伴舞,除了病人外,對員工及眷屬也算一種慰勞。雖然我們行動自由,但是因公路巴士的班次很少,到新莊街或台北市都很不方便,我們住的地方真是所謂的寨村。院方也利用空的眷舍做俱樂部,裡面放一台撞球台和圍棋等設備,但很少人利用,其他沒有什麼娛樂設備。
過新年的日子
每年元旦(新曆)的前幾天,員工的太太們會在院長宿舍的後院集合起來搗製年糕,準備過年時食用。那種東西現在新曆元旦時可以在義美或大型百貨公司買得到,目前在日本由自己做的也已經不多了。元旦時氣候很冷,晚上在火盆烤年糕吃,有很特別的味道。
由於這個眷村是不小的社區,而且工作都在同一個地方,過新年互相拜年時,對方可能也出去拜年不在家,所以習慣上我們會在玄關放一個漂亮的淺盤互放名片,以表示已經來拜過年了。
過新年時,像我們做醫院醫長的家就不簡單了,家母在幾天前就開始準備很多菜,以便當日招待同事們。日本人很會喝酒,有些人一喝醉就醜態百出,有一次竟然有人站在屋簷下的走廊向後院小便。家父不會喝酒,假若和他們一樣地喝酒,很可能會讓他縮短壽命。這種習俗在過去的台大醫院也有,科主任過年時請醫局的人到家裡吃飯喝酒,並訓練年輕的住院醫師喝酒。現在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很注重個人的生活品質,大概不會再這樣鬧酒了吧。
白天年輕的女性員工,以及員工的女兒穿上最好、最漂亮的和服,到院長宿舍前照相,我家還留有一些照片。她們玩拍毽子板,在家裡玩歌兒多(日本紙牌)、吃年糕。男孩子們沒有特別的玩法,記得有放風箏。戰前是放買來的風箏,很會飛;後來學校工藝課教做風箏,大概我做的風箏太堅固重量太重了,都飛不起來。那個時候雖然我們及附近的小孩都沒有紅包可拿,但還是覺得過新年是很快樂、很好玩的時候。
樂生療養院也鼓勵病人玩樂器,偶而聽到豎笛、簫還有胡琴的聲音,夜間除了少數的路燈外,整個眷村都很暗,這個時候聽到胡琴聲音,實在令人快樂不起來,弟妹每次聽到這個聲音都會緘口不語。
日本皇室的重視
日本時代大家都認為癩病是不易感染,但一經感染是很不容易治癒的疾病,一旦被收容在樂生療養院,大概不會有痊癒出院的機會。所以該院的員工進入治療區域時都需要換衣服,這種衣服類似前幾年SARS流行時醫護人員所穿的防護衣服,還要經過消毒藥水池,消毒長筒靴,出來時也一樣要經過消毒。
就當時而言,樂生療養院的設備大概是經專業人員設計,相當現代化,有很大的鍋爐以消毒醫療器械、煮飯、洗衣之用,也有專人在燙布類。伙食好像可以自由選擇自行調理或由中央供應,在那個時候該院的廚房就已有大型的不鏽鋼煮飯器。
日本人認為癩病病人的存在是國恥,所以一發現癩病病人時就用警力強制收容,但是收容後給予良好的生活環境,盡量安撫,尊重他們的自尊,使他們安靜下來。
日本皇室對癩病很重視,經常捐贈金錢及物品,因此院方也不敢馬虎。大概於本人小學1-2年級時,家父赴日參加全日本癩病醫學會,當時的日本皇太后特別召見並鼓勵有加,贈送療養院一些楓樹的樹苗,並給家父香煙及皇室特有的銅鑼燒及落雁(日本米糕),上面蓋有日本皇室的菊花紋章,院方將之視為無上的光榮,回台時全體員工及眷屬列隊恭迎皇太后的御賜品。如同名人種的紀念樹苗一樣,這些楓樹苗好像水土不服,一直到本人離開樂生療養院時都沒有長高多少,後來如何就不知道了。
到了二次大戰末期,物資的供應越來越困難,病人與他們家人關係越來越淡薄,寄送的東西也越來越少,能自行活動的病人,還可以種蔬菜、養鷄養鴨勉強過活,後來越來越無法忍受時有人會逃跑。當時日本警察網很嚴密,很容易被抓回來,而家鄉人的排斥報警,也是另外一個原因。抓回來就關禁閉室,警衛並給予體罰,大概用鞭子打。因為禁閉室離我們的宿舍約300公尺,中間沒有什麼建築物,所以鞭子的聲音都可以清晰聽到,跟著即是病人的哀叫聲。而這位警衛不知是否為了這些事情,大戰結束後被附近的居民活活地打死。記得那天我們一起搭公路巴士從台北市回來,我們先下車,等到他下車時一群附近的居民就圍上來,用木棍狠狠地打他,不到幾天他就死了,遺體在院附設火葬場火化,骨灰可能由其他的日本同事帶回日本。
樂生病友、員工子女之學校生活
該院有一所「保育園」,是收容住院病人子女的地方,最大的大概到小學畢業為止。台灣人及日本人都有,可是台灣人較少。他們本身沒有感染到癩病,但因為父母有這種疾病,親人或附近的居民都不太接受,所以由該園收容,可以一邊上學並偶而與父母見面。本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園兒,是小學高我一年級的男孩,他似乎有音樂天才,每次療養院放電影後的第二天,他就可以在學校的風琴彈出該電影的主題曲,沒有樂譜也沒有人教,但\他憑記憶就可以彈出來。他於小學畢業後報名做日本軍事工廠工員,後來被派到菲律賓服務,戰後,接到他由日本來信說已安全回日本。另外有一個女孩,與家妹同年齡,小學也同班。終戰後,因為她在日本無依無靠,由附近的農民收養而沒有回日本,也不知其目前之情形。
本人參加中國時報記者張平直於該院舉辦的新書發表會時,特地到舊日的保育園,發現該建築物完全和以前一樣,一點都沒有改變,一時真有時間倒流的感覺。員工眷村的兒童到了學齡時當然要上學,日本兒童上新莊街的新莊尋常小學校,台灣人則上新莊公學校,後來日本人的學校改名為「新莊國民學校」,而台灣人的學校改名為「新莊東國民學校」。終戰後,新莊國民學校改為中學,據說日本有名的小說家陳舜臣回台期間,有段時期曾在這個中學擔任教員。
由於父親留日,母親是目前中山女高的前身—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畢業,曾擔任南部公學校教員,而眷村大多是日本人,所以我從小就會講日本話,因此申請入日本小學校讀書。但因為我是台灣人,無法無條件入學,需經過測驗後才能以「共學生」(共讀生)的名義入學。據說,測驗時老師給我看撢子的圖樣,問我這是什麼?我當然知道它是一種清潔用品,但它同時也是家裡小孩做錯事時母親拿來打我們的東西,在我印象中它做為鞭子的功能比清潔的功能還大,因此我很自然的回答那是鞭子。也是一樣做過小學老師的母親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她聽到這個回答覺得很不好意思也很尷尬。
當時住在新莊郡的日本人不多,而且新莊街也不很大,只有向南北的一條街,大部份的學童父母在新莊郡的郡役所(鎮公所)做事,所以學校很小:只有一個禮堂及三個教室,一個存放體育用具的倉庫及單身老師的宿舍,校長在附近有單獨的宿舍。一個教室有二個年級的學童上課,這是所謂的複式教育。我記得家兄畢業時只有3位畢業生,姊姊那一屆也差不多只有3位畢業生,本人畢業時因為有從日本宮古島和與那國島疏散來台的學童,而多了幾位學生,最遠的是由現在的三重市來上學的。包含保育園的日本學童在內,來自樂生療養院的學童有5-6位,我們一般都搭公路局巴士上學,但因為班次不多,有時候療養院的公務車因公到台北,我們也會搭公務車的便車。公務車本來用汽油,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裝成木炭車速度不快。公務車分開為兩區,我們坐前半段,由前門進入,中間有玻璃牆分隔,病人坐後半段由後門進入。以當時我們的速度,由新莊街走到樂生療養院眷村約需1個小時,我在天氣好的時候都步行回家。
感受台日的差別對待
小學低年級時,我們沒有感受到台日差異,到了高年級時,慢慢感覺到台日的差別,日本同學也感受到這點,會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優越感。母親知道這一點,所以嚴格監督我們的言行,不能表現得太差,否則會被孤立,不僅在眷村的生活難過,在學校更難過。父親常跟我們講"韓愈胯下之辱"的故事,要我們忍耐。正如同有人曾經說過,在那個時代我們台灣人必須表現得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終戰後本人在台大醫院任職,由於本人會說日本語和英語,時常接待來院參觀的外國人。有一次接待一位菲律賓醫師,他曾問我戰前日本對你們台灣人不好,為什麼你們還對日本人那麼好?我回答說我們現在已經不是過去主僱間的關係,而我們在享受平等的交際,平等的對談關係。
小學4年級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日戰爭則早已開打多年。雖然我們社區有位日本工作人員被徵召當兵在中國大陸戰死,但台灣人是日本三等國民根本沒有被徵召的資格,只有少數人去做日軍的文職工作人員,所以戰爭對我們小孩來說幾乎是沒有影響的。可能有些物資有缺乏的現象,我們小孩子也沒有感覺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物質缺乏漸漸明顯,而且日本政府嚴格控制,有的東西在街上根本買不到。有一次本人看到有位台灣籍的刑警在新莊街公路局車站查一位台灣老太太的行李,在裏面找到2台斤的花生米,就將這位老太太帶走了。
昭和20年(1945年)大約是4-5月左右,我曾好奇地去目前的中山市場,也就是當時的御成町市場,對面的大正街是當時台北企業界日本大人物住的地方,是一個很有日本味的市場,就像現在的士東市場,可能比士東市場還乾淨。我進去那個市場時什麼東西也沒有,只有一群群帶著「愛國婦人會」肩帶的婦女在一葉一葉地扒高麗菜,一片一片地切南瓜,並做配給。其他則空盪盪一個人都沒有。
那個時候要買全棉的衣服或布料很難,毛料是幾乎不可能買到,只能買到棉成分很低的人造纖維的衣服或布料。其品質很差,一洗就軟綿綿地衣服會走樣,穿起來更是不舒服。而在本人小學5年級時,日本政府-可能是台灣總督府,突然大發慈悲地開始配給學童全棉的制服,同學很高興地排隊領制服。輪到本人時,老師說這次只配給日本人,下次有包含台灣人時一定給你。當時本人很傷心,因為我知道全棉的衣服在街上根本買不到,如果我能配到全棉制服拿回家,家母一定會很高與。回到家父母聽到這個事情時,沒有講什麼,也沒有生氣,只有苦笑。在往後的節慶,日本人都穿著全新的全棉制服,只有我們幾個台灣人沒有,這個時候才感覺到台灣人與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此後到戰爭結束,不論台灣人或日本人都再也沒有機會分配到制服了。但是他們日本人於終戰後,被遣送回國時倒有以前配給的全棉制服可以穿。
日治時代新莊每年有一次全郡學童(包含高等科)的運動大會,台灣人的公學校部份與日本人的小學部份是分開比賽,同樣的學童,同樣的年齡,為什麼要分開?其理由就無從而知。很可能是新莊郡公學校學童大部份都是農家子弟,無論體力或耐力都比同年齡的日本學童好;日本學童的家長大部份是公務員,其生活水準較好,但體力及耐力也差一點,比賽時贏的機會不大,輸了又讓家長難堪,所以就乾脆分開比賽。
實際上台灣人離開台灣人的人群,進日本人的小學做共學生,外表看似可享受很多特權,實際上很不簡單,所受的精神壓力很大。
小學畢業考取台北州立台北第三中學時,為了我這個新小大人,母親特地拆了沙發椅套,以DIY方式染為綠色—當時的中學生制服為綠色,請人縫製台北三中的制服。這是本人頭一件長褲子的衣服,當時因係DIY染色,所以濃淡不一,好像目前軍中的迷彩裝,因不久即日本戰敗,真正有機會穿它是編入建國中學以後。
戰時物資缺乏
由於台灣不產棉花,棉布的缺乏是全島性的,日軍後來成立的新部隊如學生部隊、整備召集部隊等,軍裝都非常地差,甚至武器也差,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槍及刺刀。聽說日本為了支援在東南亞作戰的部隊,日本軍一船一船的運送軍人及武器,結果連人帶武器都被聯軍的潛水艇炸沈。這個情形在日本本島也是一樣,最近NHK電視台講述有關昭和20年(1945年)6-7月的情形時就提到這一點。食物運送的情形也一樣,由台灣供應東南亞作戰部隊的糧食,到了後來運糧船也是一艘艘地被打沈,即使以漁船運米也被打沈,最後甚至沒有船可以運糧到前線。而且聯軍的戰機經常炸火車,島內的糧食運送都不順利,加上各地區的警察管得很嚴,所以有的地方物資糧食很豐富,有的地方則什麼都沒有。我們遇到的一個特殊的例子是,戰後有位朋友由嘉義布袋港來,戰時那兒牡蠣盛產,運不出去,人吃膩了,只好將吃不完的當飼料餵養鷄鴨,而我們在那個時候則看不到一粒牡蠣。
小學高年級正是成長的階段,食量很大。同學一起聊天的時候常聊到吃的東西,有一天聊到當時在台北市很有名的糕餅店「一六軒」,記得是在現在的重慶南路或博愛路,大約就是在日本店集中的地方。有位同學說那家店為了防備小學徒偷吃,所以一開始就讓他們無限量地吃,直到吃膩為止。大家聽了很羨慕,都希望畢業後能到該店做小學徒而大吃特吃,結果沒有一個人去那家店做小學徒。
我們利用每一塊空地種蔬菜,甚至冬天租用附近的稻田種白蘿蔔,由於我們沒有種子也不會種,都請農民幫忙而由我們照顧。收穫時蘿蔔葉差不多都給蟲吃光了,但是大部份的蘿蔔都可以收成,母親做了很多的蘿蔔乾,那個時候我們家的蘿蔔乾是隨時可以吃的,沒有任何限制。母親做的鷄蛋炒蘿蔔乾,不像現在餐廳賣的放那麼多鷄蛋,我們那時候常夢想如果能多用幾個蛋多好。粥飯也是一樣,蕃薯都比米多。除了種蔬菜以外我們也養鷄、鴨、鵝,甚至火鷄。我們早晨還要到田野抓「食用蝸牛」,這些食用蝸牛,聽說是日本人為了改善台灣住民的營養問題,特地老遠由南洋進口並命名為「食用蝸牛」,不久即擴及台灣全島養殖。結果台灣人不敢吃,反而這些蝸牛吃我們種的蔬菜。但是家禽類都很喜歡吃蝸牛,抓回來後將它打碎後就爭著搶食。雖然如此,這些鷄鴨長到能吃的不多,會先開始打瞌睡,然後一隻一隻的倒下去,連體型很大的火鷄都如此。
當時台北三中(現在的師大附中)校舍被日本軍徵用,我們到台北一中(現在的建國中學)與他們分兩班制上課。1945年4月1日台北三中入學典禮後,學校宣佈因為空襲,在台北市很危險,暫時可以不需到學校上課。對本人來說這是一段新生活的開始,那時和考入台北一中的林姓同學在南京西路六伯父家共同生活上學。其實,開始時聯軍空襲台北市的次數不多也不嚴重,但是由於老師及高年級學生都去當兵,學校內沒有什麼老師,也沒有課本,所以沒有什麼課可以上,大部份是軍訓、劍道或勞動服務,但對我這才開始新生活的人來說,還是相當快樂。同年5月31日台北大空襲,我們從防空洞出來時台北市到處失火,據說台北一中及總督府都被炸,我們只得連夜趕回眷村。後來學校借用板橋國民學校校舍開分校上課,但還是只有軍訓課及精神講話而已。
在本人記憶中,有一次因搭不上班次很少的公路局巴士,從板橋走路回家。從縱貫公路進入眷村路旁的曬穀場上有一位日本太太在曬稻穀,旁邊一間簡易存放農具的茅草屋,有幾個小孩子在玩耍。那位日本太太的大兒子與本人同年,其他的孩子都還很小,她的先生在樂生療養院工作被徵調當兵去了。當下我沒有什麼感想,近日再回憶當時的情形覺得很感動。因為日本人多少有殖民地主人的架勢,自尊心很高。絕大部份的農民是台灣人,所以除非政府命令的勞動服務外,絕對不會自動幫忙農事,更不會受僱於台灣人。由於日本人終於承認兵源不足,讓台灣人「升格」可以當天皇的臣民,許多年輕人被徵召當皇軍去了,所以農村也是人手不夠。那個時候雖然糧食缺乏,但農民對幫助收割及曬穀的人很照顧,不僅提供三餐還有兩頓點心而且全是大魚大肉,是其他的地方吃不到,也歡迎小孩子一起吃,當然還有一點酬勞。本人感動的地方是,那麼熱的天氣之下,為了照顧及保護自己的小孩,寧可做殖民地人民的僱工,來賺點家計並讓小孩飽食幾頓。另外本人覺得她很幸運的是聯軍沒有在台灣登陸,由於人在戰場都會變得非常自私,這些先生沒在身邊的軍眷一旦被捲入戰場時,誰也不會來管這些軍人眷屬的安全。
最近日本NHK電視台播放的有關昭和20年(1945年)6、7月的回憶中,有人的日記曾經提到,當時日本大阪地區的防衛司令竟然說出:假若美軍登陸日本時,應將老幼婦孺綑綁手腳先予射殺。如果這事屬實,美軍若登陸台灣,我們這些三等國民台灣人,及那些先生在日本軍中服務的軍眷,都會優先被射殺,以免妨礙日軍的作戰,根本別談保護了。有興趣探討史實的人,應可到日本查台灣軍司令部或者大本營的政戰資料。
這種情形下,另外更可憐的一群人是癩病療養院的病人,療養院能提供的物質很有限。這些弱勢人群完全處於被動情況,好的時候很好,由各地來的捐獻十分充足,但情勢不好的時候則什麼都沒有。依照國家規定配給,肚子餓了,只能說很抱歉這是國家的規定,戰前戰後,不同的政府有相同的作法,沒有人能給予同情。能夠走動的人,可以種菜、養鷄鴨,日子還算可以過;那些不能自由活動的人就更可憐了,需靠其他人的愛心分享。那個時候藥物亦缺乏,沒有現在所謂的特效樂,只靠注射一種名為大風子油的藥品,但其效果不明顯,病人對未來沒有任何希望。餓得發慌的病人常逃回故鄉,但是日本警方的組織很嚴密,而且家鄉的親朋也不願意收留他,大部份都會被抓回來,並被關禁閉及處罰,這是一個很悲哀的時代。
由於我們對農事不在行,所種的菜及所養的鷄、鴨總不夠吃。最後母親只好拿衣類與附近的農家交換鷄蛋,還好戰爭沒有幾個月就結束了,否則我們將會沒有衣服可穿。
離我們家約30分鐘的地方,約有30多名學生兵部隊駐守,這部隊大概是新編部隊,所以配備及物資的補給都很差,營房是DIY的稻草屋,主要的工作是構築陣地。這些學生兵都是大專生,因為年輕食量很大,軍中的伙食永遠不夠他們吃飽。他們下工回營房時必經的塔寮坑頂坡角只有十戶左右的小街,雖說是小街,但有一家較大的雜貨店,除賣乾貨外還兼中藥店及碾米廠,所以光是他們就佔了3間店面,是那一帶最富有的人。小街還有一間小理髮店,一家只有一張小桌子的麵店,及一家專賣兒童小玩具及零食糖果的小店,主顧客為小孩。幾乎每日下午學生回營時,都會買附近農家利用剩糧製作的糕餅,雖然使用的是配給糖,甜度不夠,但對餓著肚子的學生兵來說,已經是非常好吃的東西了。這些學生兵的家境可能都不錯,買這些東西不成問題,所以每個人都可以買好幾個,而吃起來就好像好久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
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我哥哥在台北三中的同學,有一次家母招待他們到家裡吃荷包蛋,看到他們的那種吃相,可能想到她也在當兵的兒子,就流下眼淚。哥哥的部隊在台灣大學內,很少能回家。
日據時代,公立醫院的醫師都很用功,父親除了做地方癩病調查報告外,為了做癩病細菌的移植研究,在樂生療養院內養了不少猴子。當時療養院對這方面的預算很充裕,不僅建造了猴子籠,而且飼料也很豐富,不像父親在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時,還要從家裡帶剩飯去餵猴子。
父親有時會到台北圖書館找資料,也帶我及弟弟一起去,讓家母專心於家事。當時的台北圖書館就在現在的交通部前面,也就是在總督府的後面,除了一般圖書以外,還有一個面積相當大的兒童圖書館,我們的興趣在兒童圖書館,那裡的書籍很多。回去前父親會帶我們到地下室吃黃豆甜湯,當時紅豆及綠豆很難買到,做豆腐的黃豆煮熟放點糖,對我們鄉下孩子來說就是很好的點心。這間圖書館在1945年5月31日台北大空襲時燒燬了,但據說當時有一部份的書籍已疏散到下而倖存。後來本人曾再去圖書館,發現還有部份燒燬的報紙散在地上,無論如何,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樂生療養院的治安一直都很好,圍牆不超過1公尺高,圍牆沒有大門,我們出門時都將鑰匙掛在門邊,也不曾聽過有小偷。本人退休後回去看以前的眷村,每家的圍牆都蓋得比我還高。
二次大戰結束前不僅物資缺乏,薪水也被七折八扣,例如勞軍捐、強迫儲蓄等等名目,讓父親真正拿回家的薪水越來越少。還好我們鄉下孩子不知道都市中曾有過的奢侈物質生活,不太感覺到貧乏的痛苦。
國民政府的接收
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開始接收台灣,父親是台灣總督府的公務員,又是台灣人,所以被徵調擔任衛生局(後來的台灣省衛生處)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台灣的公共衛生與接收公立醫院,所以經常上台北市。父親小時候雖上公學校,但下課後還要在家學習中國古文,所以北京話雖然聽講不怎麼好,但讀寫還是可以的,這一點就比別人有利。
父親遇襲-離開樂生療養院
戰爭結束後的某一天,父親搭公路局巴士赴台北市工作時,突然受到眷村外居民用竹棍襲擊,還好坐在旁邊的一位護士小姐奮力用手阻擋,結果父親沒有受傷,倒是那位護士受了一點外傷。事後我們研究了半天,實在想不出原因來,因為父親不但把全部的年終獎金捐給院內保育園的孩子和病人,甚至還經常捐錢及東西,附近的居民生病時,他也是只要有人叫,三更半夜都會趕去為他們看病。後來才知道,因為父親是日本政府公務員,又是醫師,所以必須參與兵役體檢。當時日本的兵源非常缺乏,本來沒有資格加入皇軍的台灣人到了此二次大戰末期,都突然被「升格」、「恩准」加入皇軍了,而日本人又恨不得所有的台灣役男都可以送去當光榮的皇軍,所以體檢都特別的嚴格,除非有特別明顯的缺陷外,都得去當兵。在這種情形之下,家父沒有機會為他們偽造免於當兵的病名。日本軍隊又一向以嚴格訓練而聞名,台灣人加入皇軍都受到嚴格的操練,所以當戰爭結束回到家後,有人就認為是因為家父沒有幫忙才會受苦,但是在日本人的嚴格監視下,這種基於愛護同胞的忙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原在眷村的生活是很快樂的,父親對樂生療養院的工作也很滿意,但是這件事發生後我們覺得安全受到威脅,只好急著離開。還好當時在台灣省衛生局(即後來的衛生處)的幫忙下,得以轉任衛生局的專任課長,比日本人還早離開療養院。但是由於國民政府知道父親不僅對樂生療養院的運作很熟悉,而且也知道一些省立醫院的情形,所以就派他代表衛生局接收樂生療養院。甚至有一段時間,因為沒有人願意出任該院院長,而只好勉強父親去擔任一段短時間的院長,還好那段期間內沒發生任何問題。
我們搬到台北後,日本人陸續離開台灣,被日本人徵召到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作戰的台灣兵也陸續回台,同時也來了不少國民政府的軍隊。不知是什麼原因,其後約有一年多的期間內,即於本人進入高中前,發生蝨子大感染。在內衣褲縫兒內都可以發現很多蝨子卵,記得有一次上課時還看到前面同學的背上有一隻蝨子在爬。據當時還留在日本的某位台大醫院教授也曾說,日本就在同時候也發生蝨子大感染。我感覺那很類似國外一些有關海盜的電影情節一樣,有時要一邊曬太陽一邊抓蝨子。
由於父親不習慣衛生行政單位的官僚作風,就轉任台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後來該所改組為公共衛生研究所。
我們搬到台北市後,當時念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的家兄,因為學制的不同於終戰後被編入台灣大學先修班,但是他認為台灣人已經不是只能做醫師或律師而已,有廣大的中國大陸及非常光明的未來,所以轉到理學院化學系求發展。但是不久罹患腦腫瘤,雖然請台大醫院的日本籍河石九二夫教授開刀,但是手術後半身不遂,過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即去世了。家姊在日據時代就讀台北第二高等女子學校,位於目前的立法院現址,後來編入目前的一女中。本人因北一中、北三中及北四中合併為建國中學,而就讀於建國中學,在初中三年級時轉學到離住家較近的師大附中,而我的弟妹則轉到東門國校。
戰爭結束-希望與失落
我們雖然知道,我們的祖先由中國大陸移民到台灣,但對中國大陸的印象模糊。當時我完全講日本話,台灣話除了父母親常講的幾句以外其他的都不會,更何況北京話。對於中國大陸,除了北京、南京、上海等幾個被日本軍隊佔領而常出現在報紙上的地名外,其他的也是什麼都不知道。家兄曾在日本人歸國前的舊書攤上,買到賽珍珠寫的《大地》日語翻譯本,雖三冊中只買到第一及第三冊,但卻是我瞭解中國大陸的入門書。該書的日語翻譯很美,我讀了好幾次。
戰爭是結束了,好像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我們都以為從此以後和平快樂,而且物資豐富的時代即將到來。但是突然間街上有錢都買不到米,家母回到樂生療養院附近的農家買米,只能靠著關係特別請求他們賣米給我們,農家看在母親是曾幫他們看病的醫師太太份上,好不容易才一點一點地賣給我們,母親找米找得很辛苦,看到她每次買米回家的辛苦樣子,我們都覺得很不忍心。而且那個時候,由家鄉嘉義市來台北辦事的親戚朋友都借住在我們家,所以米的消耗量很大,除了便當以外,在家裡都吃粥。後來親戚朋友發現了我們的困境,每次到家裡來借住時,都會帶一斗米送給我們。這種情形就好像在戰爭時候,即我小學五年級參加學校的旅遊活動(他們稱這為學習旅行),到中南部時也要帶米參加。這種情形發生在光復後,而且是戰勝國的台灣就很奇怪。日據時代糧食管控得很嚴格,台灣是日本的米倉,應存有大量的戰備米;而且農民還在持續生產中,米應該是有很多,不可能會缺米缺到這個程度。後來我們才知道,有人將台灣的米拿到中國大陸販售,這樣小的地方生產的米,供應大陸那麼大的地方,即使餓死所有的台灣人也不會夠的。
戰後人謀不臧與困苦的經濟生活
這個時候的樂生療養院的病人體驗到另外一個痛苦的經驗。雖然光復了,體會光復甜蜜滋味的時間很短,當時的政府對癩病病人的補助也是依法辦理。而他們所謂的「依法辦理」,就是以很清高的姿態:就只發給這一些,夠不夠會不會餓死都不是我的事。戰後中國大陸來台的軍人也發現不少癩病病人,也住在該院,他們曾發動過幾次抗爭事件,據說因為抗爭的行動太過激烈,使得當時的院長上班時需備手槍自衛。當然有些病人認為已經光復了,不應該管得如過去日本人的時代那麼嚴。本人也很同情他們,雖然也有中國大陸來的癩病病人,但當時的政府官員大概無法瞭解關在樂生療養院幾十年的病人心理。我父親雖然已經離開該院,但仍有老同事會來我家訴苦,我們也是無可奈何只有聽聽,甚至於在幾年後有人到日本,還向日本的老同事訴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是我家經濟上災難的開始。家父以前除了薪水外,還有一點嘉義祖傳田產田租的額外收入。日本人離開台灣後,那些佃農不願再給我們田租,田地在嘉義,佃農也在嘉義,那個時候的交通慢又不便,我們寫信催繳如同白寫。佃農們大概認為台灣光復了,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也光復了不必再給佃租了,根本沒想到家父公務員的薪水會那麼低,實在是很需要那些佃租補貼。我們那個時候很辛苦,連買一部中古的腳踏車都成問題,而我的第一隻手錶是在我進入台大醫院任職後才買得起的。中國大陸當時有多名作家形容中國大陸的農民為地主勒索的對象,地主殘酷地虐待佃農。但是我覺得我們反而是被佃農欺負,家父雖然是醫師又是公務員,也是毫無辦法,只好賣掉一些傢俱補貼家用。
除了沒有錢以外,當時的通貨膨脹也是很厲害,我有一個家裡從商的同學,他曾經說:若一個東西以100元買進,再以200元賣出未必能賺錢,需要東西賣出後所得到的錢,能再買進兩個同樣的東西才是賺錢。有一次本人在二二八公園(即當時的新公園)看球賽時,看到一個軍人拿著一個裝滿紙鈔的籃球網袋,大概是他的薪水,而依當時情況估計這一大袋的紙鈔沒有幾天就會用完。當時物價變動得太快,紙鈔不夠用,很多人就乾脆使用可以任意填上金額的本票。大概本人高一的時候,有一位同學說他要去看電影,另外一位同學就問他:「你有錢嗎?」他就拿出幾佰萬元的本票給他看。那個時候不論是大陸來台者或台灣的學生都沒有多少零用錢,連最愛吃零食的女生到福利社也不敢亂花錢,一次只買幾個李子蜜餞,可以在嘴裡含很久。
因為上述的情形,家父在民國41年出版「中國癩病史」時,實在籌不出錢來,只好出售部份祖傳田產付印。
本人考取淡江英專時,英專一學期的學費差不多是台大外文系四個學年度的全部學費,家母只好標會籌措我們的學費。父親在療養院時雖然診治不少一般病人,但他還是不願意在家看診,他堅持公家機構的醫師不能在家看病人賺錢的原則,並始終遵守這個原則。當時公立醫院的醫師大部份很優秀,很多人利用下班後的夜間在家開業,有的醫師甚至在中午休息時間趕回家去看診,使得有些醫師在自家就診的病人遠超過到醫院看病的人數。這種醫師在家開業診治病人的行為,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物質消費水準。
終戰初期,有位任職總督府醫務局衛生課的日籍醫師,找到家父並打算給他一批日本政府的戰備醫藥品,以酬勞家父在樂生療養院的長期服務及貢獻,並要求家父開業賺錢。家父拒絕了,家母也很反對。如果那時候家父接受了,可能就賺錢了,也可能運氣不好被關起來。的確,那個時候有人偷賣日本人的戰備物資而賺了很多錢。那位日籍醫師很快的就在目前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近開起內科診所,但不久就被遣返日本。
根據上海東方城市影業發展有限公司的文獻紀錄影片「1949,中國」,日軍投降後負責接收日軍軍品、日本民間資產及南京偽政府軍品物資的國民政府官員操守非常地差,引起當時中國人民很大的不滿,也成為赤化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動力。同樣地,派到台灣來負責接收的官員與國軍官兵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的行為引起了台灣人的普遍不滿。事實上中日戰爭開打後,台灣人民的言論與民生物資慢慢地受到日本人的嚴格管制。在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無論言論上或生活消費物質上是最困苦的時候。日軍投降後,在台灣的日本政府解除了一切管制,讓台灣人民短暫地享受了好幾年來沒有的豐富生活。幾個月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官員及軍隊來台工作後,一切情形又倒退了。事實上不論時間的長短,人民一旦被放鬆管制,享受過自由而豐富的生活後,要再緊縮到以前困苦的生活是很難的,而且一定會發生反彈,這可能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最大原因之一。
民國94年11月6日,日本NHK播放的「昭和20年的當天」節目中,有人說他在台北松山機場擔任日本飛機機工隊的士官長,於投降後國軍還沒有開始接收前,曾有兩位國軍將軍到營房要求他們派兩部軍車,結果他發現這兩位將軍是要日本兵幫他們搬運私貨到黑市販賣。本人在民國43年受預備軍官訓練時,被教導凡是能升到將軍者,都必須人格、體能、軍事修養及操守都是最好的,這好像是與事實不相符合。
保留一個時代的紀錄
記得樂生療養院內有一座與人等高的原住民木彫像,還有一艘長約3公尺寬約40公分深具原住民風味的木舟,原來是放在走廊上。上次本人參加張平直小姐的新書發表會時,該院的工作人員說,木彫像好像移到院長室,而木舟已不知去向。那種木舟除非被故意放在露天受風吹雨打,否則應不會自行解體,很可能是被人拿走了。本人不知這兩件作品是否具藝術價值,但70年以前的作品應該收藏保存,如果是被人拿走了,希望能還給樂生療養院典藏。
最近報紙及電視常提到為了捷運的延長,樂生療養院與眷村都要拆除。三年前我妹妹從美國回來時,聽說兩個地方都要被拆除了,所以特地去看看。那個時候還有少數人住在裏面,大概有一段時間沒有整理,樹木長得很茂盛。等到新書發表會時再去,樹木已經完全砍掉了,但主要的院舍與病舍沒有很大的改變,只多了佛堂、基督教堂及改建的大禮堂。由於景物依然,小時候於星期日被父親拉到他的辦公室,罰寫毛筆字的房間還在,站在裏面深刻地感覺時光倒流。在台灣目前還保存日據時代舊建築樣式的所謂省立醫院,只剩下這家樂生療養院而己。
本人不是醫師、社會學者或公共衛生學者,只不過是成長在這個地方,很多文化工作者都主張保存樂生療養院,我也覺得樂生療養院是值得保存的。並不是為了表揚日本人為防治癩病所下的這麼多心血,只是保留一個時代的紀錄。而且,這麼大規模的一個地方,一定可以在醫療史上留下見證。台灣的癩病快要絕跡了,但是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有癩病病人的存在,據說癩病病菌的潛伏期很長,誰能保證台灣不會再有癩病?是否最近發現癩病都一律可以在門診治療,得了這種病就可以像感冒一樣的輕鬆治療?現在檢疫機構能不能完全徹底地篩檢出癩病病人,台灣有多少醫師可以診斷出癩病?
最近在電視上介紹新的樂生療養院,構造好像是普通的醫院,舊的樂生療養院是家庭式的,或許現代醫學已經發展到不需以家庭式的病舍做長期治療。但是那些已經在樂生療養院住了20-65年且行動不便的老病人來說,搬到新式醫院不見得是一種恩惠。事實上如果附近方圓數公里的地方沒有較大的醫院,且需要提高其醫療品質的話,改建為區域醫院是很正確的。但那些老癩病病人絕對不會對新醫院引以為傲,因為他們還要用一段時間來調適,以適應在新醫院的生活,這是他們難以接受的主要原因。
如果目前要他們回歸社會,最大的困難是他們的形貌不一定會受社會的歡迎,目前的社會上仍有不少思考很不科學的人存在,說不定走在街上時會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不定會被做為替罪的羔羊。所以還不如由他們自己選擇,是否願意留在舊院舍過著原有平安簡陋的生活。這個社會很不公平又自私,發現他們罹病時強迫他們住院,並與社會隔離;甚至曾經對他們的外出做處罰,當做垃圾般糟蹋。而且還有人形容這種疾病是歷史上最久最惡毒的疾病,儘量避開並拋棄這些病人,儼然成為宗教人士表現慈愛心的方式。但是現在發現這塊土地有利可圖,馬上變了一個臉趕他們出去,替代地給他們不見得住得慣的高樓大廈,據鄰近的有一個國家,遵重他們的意願,答應不會趕他們搬出病舍。這個社會卻視他們為不值得同情的弱勢人群。本人想請問那些參加策劃的捷運官員及民間人士們,即使知道現在這些病人再感染給別人的機會已經很小了,他們有沒有勇氣、有沒有慈悲心、敢不敢去做這些病人的雜役志工?
中國時報記者張平直小姐在樂生療養院新書發表會上,陳水扁總統不但蒞臨致詞,還和病人一一握手。本人看了十分感動,很可能本人對癩病的看法還停留在60年前離開眷村時─就是它是會感染的。而總統竟然會和他們握手,這簡直是意想不到的事。現在談保存樂生療養院或許沒有太大的希望,但是還有300多位病人,希望不要以強勢無情打擊弱勢的做法,任意傷害這些病人的心。
本文委由台大醫院秘書室杜芸芸小姐、呂怡燕小姐輸入電腦,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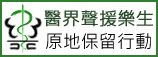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